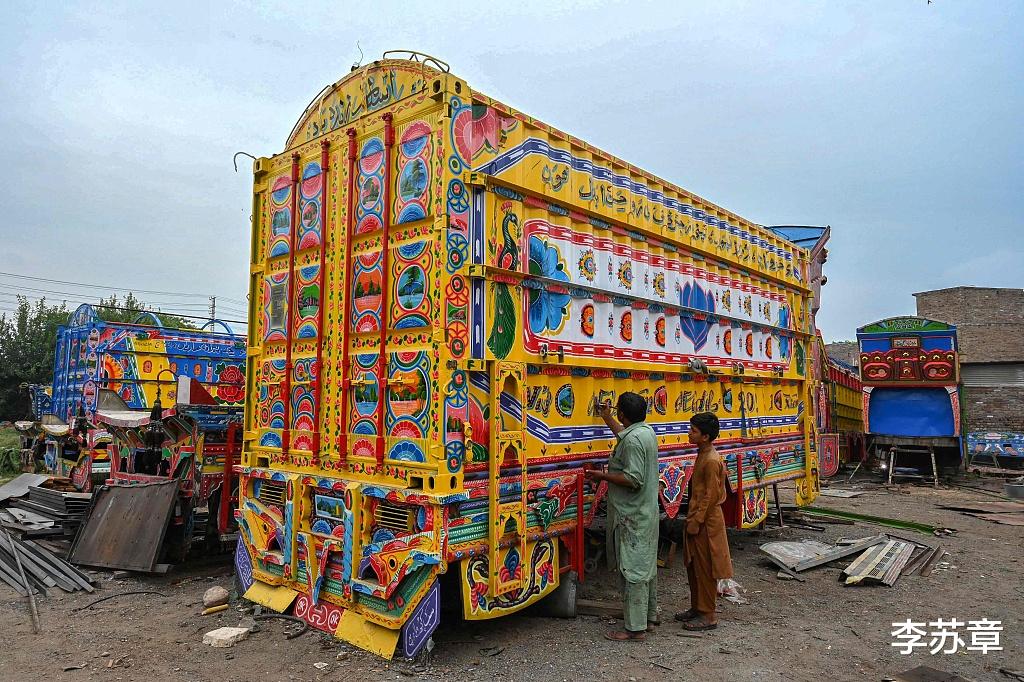
客家人居住在深山密林中,是没有工厂的。
但到了六十年代还是出现了。
它就是五.七工厂。
它应该是时代的产物。
那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办五.七干校,五.七农场。
客家地方不是世外桃源,于是乎,来了一个五.七工厂。
这个工厂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直到十多年前,修水库,才把它淹没在水下。
水可以掩盖物体,却掩盖不了记忆。
记忆中的五.七工厂还是很壮观的。
它位于去江口山区的路上,下面有一个几十米的水潭。
传说深潭面有水猴子,会抓人,尤其喜欢抓小孩,抓到了就吃掉。
我从来没有遇到,但还是有点怕。
怕水猴子突然窜岀来,把我拖下水,活活淹死。
淹死是非常恐怖的。
小时候,我们经常游泳,经常在水下面钻竹排。
有一次,钻入竹排下,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找不到出口。
开始还不慌,因为还有一口气,可以挺住,过了几秒钟,不行了,心里发慌,头脑迅速缺氧,紧接着,头部全身剧烈疼痛起来。
这种疼是撕心裂肺,痛不欲生。
让人异常地绝望!
后来还是钻了出来,但这种绝望终生留存在记忆里,因为太难受了。
当时有枪的话,我会毫不犹豫掏出来,一枪把自己崩了。
所以,我一般不轻易去这地方。
五.七工厂不一样了。
这地方非常大,应该有二、三平方公里。
前面是两栋厂房,中间是食堂和铁炉,后面是职工宿舍。
如此的规模,跟现代化工厂来说,似乎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毕竟我们这地方是山区,有这么一块平地,也是属于比较罕见的了。
这个工厂最早是锯木头,生产木板。
山上都是巨大的树木,而外面又急需木板,于是天天加工生产。
锯好的木板顺流而下,因为河道与茶陵县城相连,所以运输还是很方便。
由于长年累月地锯木头,产生了大量的木屑,倒在厂外有几十米厚。
开始大家认为是废物,无人关注。
后来有人注意到了,因为这些木屑可以用来烧火做饭。
其实,大家早就知道木屑可以烧,只是大家用的都是柴灶,木屑不耐烧,而且压在里面,只有火星,无火苗,火力不大,没办法用。
后来有人对柴灶进行了改造,专门造了一个木屑通道,让木屑在空中燃烧,如同烧木柴。
这就太太的好。
堆在厂外的木屑顿时成了抢手货,天天有人来拉。
这种状况维持了几年,后来不生产了,改炼钢铁。
厂里建有一个高铁炉,下面有一个发电厂,因此火的来源不是木柴,不是煤碳,而是电。
就是一个电锅炉。
炼铁的时候,发电机呜呜地响,电炉也传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声震几里,让人心惊胆寒。
客家山区不生产铁矿石,钢铁的来源就是从家家户户收集的废铜烂铁。
投进去的是铁,炼出来的同样是铁,只不过化成了铁水,倒入一个沙模,冷却之后,成了一个烤火用的铁盆。
这个铁盆很受客家人欢迎。
这里是高寒山区,到了十一月,山里就变得非常的寒冷,家家户户都需要烤火取暖。
以前用的是木盆,木盆放入炉灰,虽然可以抵挡传出的热量,但还是容易烤糊。
所以不好。
铁盆就不一样了。
就是把人烤得冒烟,它也没事。
它唯一的缺点就是经久耐用。
也就是说,一个铁盆可以用几十年,一辈子也差不多。
很快问题就来了,铁盆卖了几年后,就再也卖不动了。
卖不出去的铁盆只好停产,于是工厂又改成了发电。
工厂在门口建有一个发电厂。
这个好。
客家人晚上照明以前用的是小竹片,后来改用煤油,用煤油灯照明。
煤油灯不好。
我们晚自习用的就是煤油灯。
这个煤油灯会冒出一股黑烟,我们吸入后,鼻孔漆黑一片,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色的。
有专家说,烟里面有强烈的致癌物质,奇怪的是,我们熏了几年,也没有见到谁得了癌症。
但我还是十分讨厌煤油灯,现在这家伙总算可以扔掉了。
至今难忘第一次看到灯光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奇妙!
家里如同白昼,外面都是漆黑一片,灯光之下,人的眉毛看得清清楚楚,最大变化是墙旮旯里都很清楚。
这个很关键。
山区里蛇很多,经常会溜到家里来,躲在墙角处看不见。
现在好了,光天化日之下,它就不敢来了。
可惜这样的日子并没有长久。
不久,一场大火把这个发电厂烧得精光。
这天晩上,发电厂正在发电,发电员却溜了出去。
走就走吧,他偏偏把冻住的柴油放在碳火盆上烤,然后就走了。
他溜出去干什么呢?
据说去找情妇了,做第九套广播体操。
这家伙应该经常这么干,以前都没有事,他认为今晚肯定没有事。
但他忘记了他的柴油。
因为他出去的时间,不是一袋烟的功夫。
他是去谈情说爱,是去做广播体操,这点时间肯定不行。
这就有点不妙了。
烤热了的柴油迅速燃烧起来,眨眼间就成了一片火海。
很快惊动了整个山寨的人。
大家都异常惊恐地跑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赶到现场时,整个发电厂烧得通红一片。
突然,一阵"轰隆隆"巨响,一股火苗向天空蹿去,足足有五十米高。
应该是柴油桶发生了爆炸。
当时,我们是站在几百米开外的稻田里,巨大的爆炸声,还是吓得我们连连后退。
事后,发电员虽然抓起来,判了刑,但我们却没有办法了。
我又恢复了煤油灯,并且坚持好几年,直到接通了外面的电。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梳子厂。
办这个厂是一群衡阳人,有十几个吧,讲的是叽里哇啦的衡阳话。
他们生产的梳子,质量还是不错,可惜客家大部分人没有梳头的习惯,就像鄙人,一年到头都不会梳一次。
梳子销路不畅,就倒闭了。
这些衡阳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以为他们都回了衡阳,结果不是。
他们很多人去了山区乡下,定居在那里,有的还成了上门女婿。
在叶坪,有一户姓廖的人家,曾经是梳子厂的员工。
见到我,他母亲很兴奋,他也很兴奋,像久违的亲人,十分兴奋地打招呼。
为什么?
他是衡阳人。
我是衡阳人吗?
不是,但我的奶奶是。
在他眼里,我奶奶是,就等于我是了。
我们是老乡啊!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自然很激动。
但是,说实话,我对衡阳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我的奶奶是住在衡阳市,我的爷爷解放前还是某党警察局局长。
这跟我有关系吗?
因为我没有住在衡阳市啊!
我是住在山区,住在饱受生活折磨的穷山沟。
一无所有,饥寒交迫,受备欺凌。
我自然很气愤,自然不平衡,自然不认。
但五.七工厂不一样。
尽管它消失了,但在鄙人心里还是有它的位置。
因为我的童年生活与这家工厂息息相关,至少去哪里玩过,也曾经是非常向往的地方。
我曾经认为这是客家人最具现代化的场所。
(李苏章原创,抄袭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