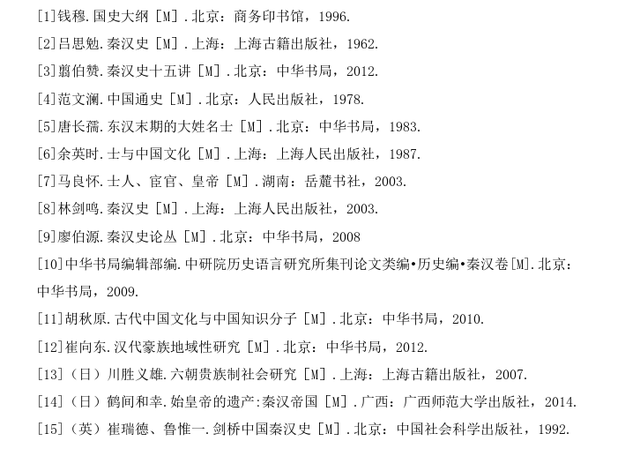文|卡门的提琴
编辑|卡门的提琴
东汉末期,一共发生发生了两起党锢之祸,惨绝人寰的政治屠杀,上演了一出人间悲剧。
当时,宦官与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已凝结成燃眉之急,然而,党人集团并未就此得逞。
相反,党锢之祸彻底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随后爆发的继位战争与起义战争终于拉开了王朝覆灭的序幕。
几百年的昔日盛世就此化为乌有,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那么,党锢之祸的起因是什么?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汉末社会矛盾加剧
汉末社会矛盾加剧东汉王朝步入和帝时期,便开启了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黑暗岁月。
那个时候,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开始在朝政上彼此角力把持权力,他们借助亲疏关系窃取国家权力,在朝野之间划分势力范围,扩张自身利益。
这种行为无疑是对正统王室权威的公然挑战,在这些人手中,东汉王朝逐渐沦为了一盘游戏棋局,他们无所不用其极地角逐、勾心斗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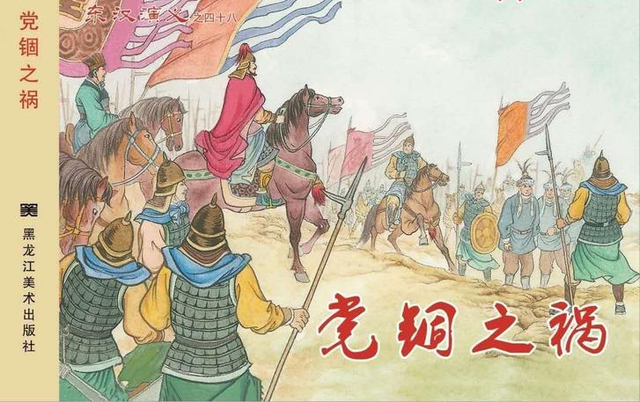
朝政日渐黑暗腐朽,民不聊生,普通老百姓在他们的欺压掠夺下,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深火热之中。
到东汉末的桓帝、灵帝时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他们操纵官员的选拔,任人唯亲,排斥异己。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穷奢极欲、毫无节制。

宦官徐璜的侄儿出任下邳令时,竟然公器私用,滥用职权,原因竟是出于一股旖旎的私欲——他热衷于追求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儿芳泽,但是却遭到了拒绝。
他竟然以职务之便,公报私仇地穷凶极恶,对李家人施加了种种非法手段和迫害,“将吏卒至暠家,载其女归,戏射杀之,埋著寺内。”
宦官曹节的兄弟破石做越骑校尉时,强夺士兵的妻子,最后逼的其妻子自杀。

宦官子弟的此类劣行不可胜数,国家权力掌握在这样的人手里,其政治的黑暗程度可见一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百姓生活的极端贫困。

延熹六年,时任光禄勋的陈蕃上书桓帝称当时社会有“三空”,即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
延熹八年,刘瑜上书言事称:“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孥相视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

甚至在司隶、豫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也出现了“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这种人间惨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政治的黑暗腐朽,在东汉末年,种种天灾也是频频发生。

仅《后汉书·桓帝纪》中记载,从桓帝即位的本初元年(146年)至党锢之祸爆发前的延熹九年(166年)的20年时间里,共发生水灾8次,地震12次,旱灾1次,疫病3次,虫灾3次。
平均每年都至少发生一次自然灾害,而且受灾面积大,发生的地点又多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方,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加严重。
除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反叛,也加剧了东汉朝廷的财政困难。

据《后汉书·桓帝纪》记载,同样是在桓帝即位之时到党锢之祸爆发的20年间,少数民族入侵达31次之多,遍布整个东汉的边境线。
与此同时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14起。
这些都使得东汉政权的财政愈加困难。

为了平息叛乱和起义,抵御少数民族入侵,东汉政府甚至减少官员的俸禄来筹措军资。
官员俸禄的减少,必然导致那些本身就贪污腐败的官员,更加残酷的剥削底层人民,以维持他们奢侈腐朽的生活。
吏治腐败、天灾不断,加上少数民族的入侵和人民的起义,都使得东汉末年的社会矛盾不断加剧,清流官员将这些矛盾的根源都指向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的宦官阶层,双方的对立和矛盾愈加尖锐,一场斗争在所难免。
 权力的争夺
权力的争夺到了东汉,由于开国之主汉光武帝本身就喜欢儒术,于是官员仕途是否通畅就和是否习儒通经更加密不可分。
在地方上,习儒通经也成为了豪族与权力结合的重要途径。

东汉后期,由于宦官把持朝政,企图经过通明经术走入政坛的士人遭到排挤,如济北相滕延因得罪宦官侯览、段珪而被免官。
廷尉冯绲杀了宦官单超的弟弟,导致“中官相党,遂共诽章诬绲,坐与司隶校尉李膺、大司农刘祐俱输左校。”
太原太守刘瓆、南阳太守成瑨因为打击宦官及其党羽而被捕死于监狱。

据统计,东汉光武帝、明帝时期,公卿95人,儒者出身36人,占38.9%,自章帝至桓帝,公卿209人,儒者出身90人,占43%。而到了灵帝和献帝时,儒者在官员中的占比下降到了35.2%和26%。
由于整个东汉时期士人阶层是在不断的扩大,而后期在官员中所占比例又在不断缩小,其受到排挤的程度可见一斑。

在党锢之祸发生后,为了进一步打击太学生,控制士人的入仕途径,昏庸无能的汉灵帝在宦官的怂恿下,在太学之外又开设了鸿都门学,来培养拥护自己和宦官集团的知识分子,士人受到进一步的排挤。
士人阶层虽有权力野心,但面对皇室统治不得不隐藏锐气,只有当朝政腐败、君主荒唐,皇权被宦官外戚把持时,他们才能借机东山再起。

表面上,士人们自诩为忠良谏言、国家脊梁。
但实则,他们也怀揣扩张权势的企图,只不过,与那些公然窃国作乱的宦官外戚不同,士人阶层更加善于隐藏野心,伺机而动。

然而,党人与宦官的斗争,本质上是国家最高统治权力之争。凭借家族优势攫取政治权力,取代宦官集团,这就是党人斗争的目的。
在王权支配下的中国古代社会,任何威胁或是侵犯到皇帝权力的行为都是王权绝对不能接受的。
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君主基本都会采取各种手段来加强和稳固中央集权,汉代同样也是如此。

从汉武帝限制丞相权力设置“内朝”、颁布“推恩令”、独尊儒术到光武帝扩大尚书台权力,都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朝中大权尽可能地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
然而随着东汉时期地方豪族大姓的发展,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逐步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清议之风掀起之后,党人凭借其名望,在地方上几乎拥有了独立于甚至超过国家司法体系的权力。
党锢之祸的导火索——“张成事件”,便是党人的领袖之一李膺在遇到朝廷大赦的政令后,无视法律,依然处死了张成之子。
此外还有成瑨、岑晊遇赦不赦杀掉勾结宦官的“南阳大滑”张汎,太原刘瓆擅自杀掉为害一方的宦官赵津。
这些事件亦足以说明党人集团所拥有的巨大权力。

同时,清议运动使得当朝权贵“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李膺的个人声誉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甚至在社会上出现了“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的现象。
这也反映出了党人的声望所影响到的已经不仅仅是宦官集团,其背后的皇权也受到了威胁。
 党锢之祸的影响
党锢之祸的影响第一次党锢之祸前后仅持续了一年就结束,对整个东汉政权造成的影响不是很大。
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了近二十年,直到到黄巾起义爆发后,汉灵帝才宣布解除党锢,大赦党人。
第二次党锢之祸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黄巾遂盛,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荡然矣。”

党人集团的本意并非是为了推翻东汉政权,他们是想通过政治改良的手段以挽救这个政权。
可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对他们长达二十年的禁锢,使他们无法对这个政权采取任何挽救措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迅速衰败到无法挽救的地步。

后世史学家也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持续太久,等到解除党锢的时候,东汉政权已然无药可救。
林剑鸣先生也认为:在黄巾起义的时候,东汉的统治者才想到解除党锢以抗拒人民的打击,这对于挽救东汉的灭亡,已经无济于事了。

在第二次党锢之祸期间,宦官集团一直掌握着中央大权,权势与日俱增,史书称其:“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贱,为人蠹害。”
即使宦官们的实际权力被剥夺,他们依旧操纵着皇帝,让皇帝像个傀儡般任凭摆布。
为了不让皇帝看见他们居住的奢华府邸,欺骗灵帝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虚散。”灵帝果然“自是不敢复升台榭。”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病死,少帝刘辨继位。
外戚何进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大权,并图谋诛除擅权的宦官张让、赵忠等人。
但经历过第二次党锢之祸的宦官,已经学到了该如何应对这种局势,他们又一次抢先行动,引诱何进入后宫,后将其杀害。

智谋不足固然是外戚失败的一个原因,但却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尤其是何进掌权时,宦官势力庞大,但士大夫阶层,却刚刚经过第二次党锢之祸长达二十年的打击,大部分已经无力再支持何进与宦官斗争。
少数有能力者,或是尸位素餐,不愿卷入新的纷争;或是另有所图,无心忠于汉室。

王夫之将这一局势分析为:“内怀夺柄之心,外无正人之助”
宦官集团长期的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必然引起新一批官僚的不满。
在何进被宦官谋杀后,握有军权的一方豪杰——袁绍站了出来。
袁绍在第二次党锢之祸时就站在党人一方,曾帮助何颙保全了众多党人。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袁绍目睹了陈蕃、窦武失败的整个过程,第二次党锢之祸后,又目睹了何进谋诛宦官失败。
袁绍吸取了党人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意识到仅凭清议和舆论是无法与宦官对抗的,要彻底铲除宦官必须依靠暴力。
他在行动时也没有像窦武、何进一样犹豫不决。在何进被杀,宫廷一片混乱之际,袁绍果断领兵打击宦官,从和帝时开始掌权的官宦集团,被彻底铲除。
 总结
总结党锢之祸是东汉正直士大夫为了挽救朝政而与腐朽的宦官势力产生矛盾,最终士大夫被宦官残酷打压的两次次政治斗争。

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两次,两次党锢之间,以窦武、陈蕃为首的党人集团短暂掌权,然而窦武、陈蕃势力与宦官的较量终以惨败收场。
两次党锢期间,大量党人遇害,整个士大夫阶层受到残酷打击,然而,两次党锢之祸并非是简单的两次同类型事件的重复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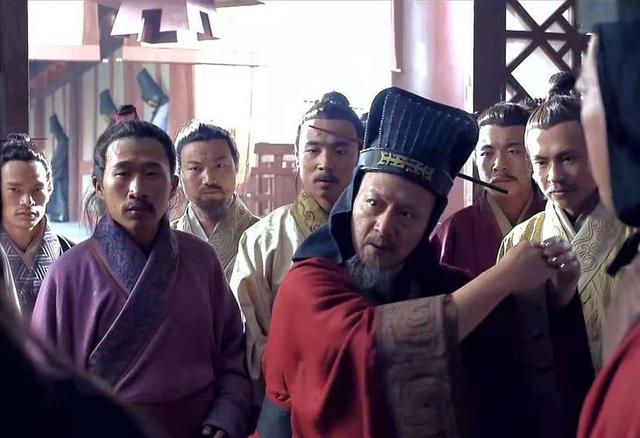
它们在兴起的原因上有相同点和不同点,在牵涉到的人群上也有区别,所带来的影响更是不尽相同。
总体上讲,第二次党锢之祸可以说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蔓延、扩大和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