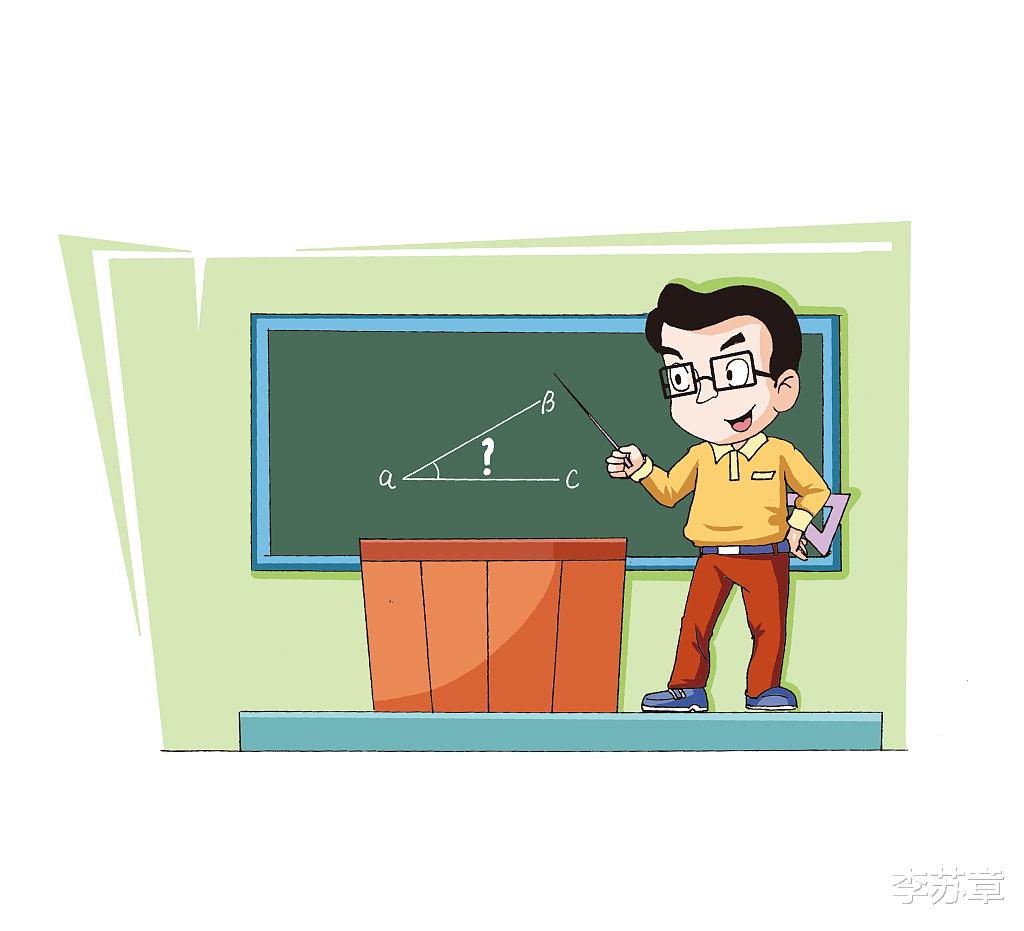
作为从小生活在客家山区的我,自然认识很多客家人。
绝大多数客家人都过着普通平凡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平淡无奇。
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默默中来,又从默默中去,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起一点泡沫。
但有一个人不同。
他是客家人的另类。
他就是凌老师。
我们都叫他凌老师。
他的确是老师。
读初中的时候,学校里有两门课有点不伦不类。
一门课是英语。
老师说的是客家山区英语,基本上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当然,我说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是现在。
现在的英语差不多成了国语,人人都会英格里死。
我也会几句,什么八格牙路,米西米西的。
我说的是日语,不是英语。
只能说现在的外国语太普遍了,一般的老百姓都会说几句。
另一门就是音乐。
老师基本上是听磁带教歌。
磁带唱一句,老师唱一句,然后大家一起唱。
走调是常态,识谱的几乎没有。
后来凌老师来了。
很快有了变化。
黑板上出现了歌谱。
他教大家唱。
我立刻发现他唱的音调很正,跟电影歌曲有差距,但很接近。
歌词在他嘴里吐出来很优美,很好听,犹如山中的泉水,发出非常锐耳的声音。
声音很美。
我由衷地感到敬佩。
其实小孩子也是有敬佩的,对有才华的人也是很敬佩。
凌老师就很有音乐才华。
可能这个才华放在县里,或者省里不算什么,但是在我们眼里只有山区,以前从来没有什么动听的音乐。
他出现了,他就是才华。
我们就由衷的敬佩。
很快,我又有了另外新的发现,他会绘画。
我以前不知道。
一天,他来到我家门口,说要借一张凳子。
我自然惊喜万分。
小孩子都喜欢帮老师做事,如果老师主动提出来了,就更加喜欢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帮老师买烟。
我家开了一家商店,而学校离商店又比较远,所以他要我帮他买。
他给了钱,需要找零。
在找零的时候,我突发奇想,多找他一分钱,看他的表现?
结果很遗憾,他私吞了。
当时的一分钱可以买一粒糖。
糖这东西是非常的珍贵,我们如果有了一粒糖,会吃上一整天。
主要是在嘴里放上几秒钟,然后迅速吐出来,等一个小时后,再放上去,如此反复,吃二天没有问题。
当然,凌老师不存在这个问题。
他就是坐一下而已,绝对不会带走。
他坐下来干什么呢?
开始我不知道。
后来他拿出了画夹,开始画了起来,我才知道,他是在画画。
说实话,山区的客家人是不会画画的,即使画,也是画菩萨老爷之类,我很不喜欢。
我以为他也是画菩萨,很快发现不是。
他在画我们的街道,并且奇迹出现了。
他画的街道跟眼前的街道非常的逼真。
当然,不是完全逼真,跟照片有差距,但很真了。
至少是我眼见最真的画。
我自然惊得目瞪口呆。
我一直以为画只在书本上,在电影里,想不到凌老师也有。
他只要一画,一幅美丽的图画就出来了。
的确让人佩服。
我以为他会一直画下去。
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不干了。
他辞职了。
他只教了半年,就不干了。
我们异常地震惊。
因为他辞职后,没有去县里,没有去省里,而是回到家里,回到一个十分贫穷落后的山寨。
他去干什么呢?
种田。
这就让人十分费解了。
当时不是现在。
当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工作是国家统一分配的,是非常金贵的一份工作。
百分之九十九的客家人都没有,如果有了,会兴奋得三天三夜。
山寨的少女会立即表示要嫁给你。
凌老师却不要了。
当时教师的工资有三十多元,而在客家农村出工一天只有二毛钱,一个月的收入只有六块钱。
而且没日没夜,累死累活。
哪有教师这么舒服呀!
当年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说。
说到这些时,老师总会得意洋洋问我们,我是什么劳动啊?
我们总会大声地喊道,脑力劳动!
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脑力劳动的确是一个好东西。
几乎是脑子一转,钱就来了。
那像我们大人,砍了一天的柴,从山上背回家,走了十几里山路,累得腰都要断了,结果就挣了五毛钱。
没想到的是,凌老师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
并且放弃得非常的坚决。
凌老师自己也讲了,当时学校的领导找了他不少七八次,要他重返校园,但他坚决不干。
这不是问题的最关键。
最关键的是,他不是升官发财。
他是去学知识青年,改天换地吗?
不是。
他从来没有想过改什么天,换什么地,而他也没这个机会。
因为他连山寨一个小小的领导都不是。
他就是从客家山寨里出来,又重新回归到山寨,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客家山寨人。
也就是,他是大山的儿子,就要回到大山里面去。
可能他就是这么想的。
当然,凌老师还是有文化有知识。
他发现种田不赚钱,养鸡养猪不赚钱,于是学起了养蜂,并且很成功。
至少生活不成问题。
又让人惊讶的是,回到山寨的凌老师并没有平静下来。
他骨子里还是有一股与天斗,与地斗的狠劲,如同他当年辞职一般,非得闹个轰轰烈烈。
晚年,他在客家人群中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山寨里需要建一个水电站,自然会占用山民的土地与房屋,但补偿价格很低。
这些钱让很多山民建不起房子,自然不服。
凌老师住的地方不需要拆迁,也不存在补偿一说。
但他就是要管闲事,带领大家上蹿下跳,与山寨斗。
斗的结果是,他入狱了,他的儿子也入狱了。
他输得很惨。
客观公正地说,他的闹有对,也有不对。
对的地方,补偿金是有点让人妈妈的,让很多客家人欲哭无泪。
但也是没办法。
客家穷,客家落后,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建电站。
因为只有解决电的问题,才能解决经济问题,才能发展生产。
问题是没钱呀。
只好压缩标准,降低标准了。
牺牲客家人的利益,换起经济上的发展,这是痛苦的选择,也是不得而为之的选择。
凌老师当了一回旗手,为客家人鼓与呼,不能说没有任何效果,至少后来的决策还是充分考虑了客家人的利益。
他在这方面还是出了力。
我们应该看到,有人说,跟无人说,效果还是不一样。
当然,历史就是这样,无论你如何努力,终究斗不过时间,曾经的辉煌终会被时间偷走,犹如他当年一样,从起点回归到起点,不留一片云彩。
说到底,凌老师终究是一个平凡的老师,一个普普通通的客家人,但是他的曾经,为客家人的付出,我觉得还是值得每个客家人铭记。
(李苏章原创,抄袭必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