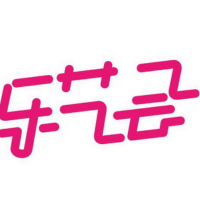二、僧伽持的什么瓶
在上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僧伽故事中,一会儿说的是澡罐,一会儿说的又是澡瓶,一会儿又称是净瓶,那么,澡罐与澡瓶、净瓶有什么关联,又有什么区别呢?
1、僧伽所持之澡罐
《乾隆大藏经 不空罥索陀罗尼经序 明主咒王成就像法品第四》有云:尔时复说造像之法。与其画师授于八戒令净持斋。当于不截净白氎上画观自在菩萨形像。诸彩色中不得著胶。作髻发色如莲华藏。面上三眼白縠络身。披黑鹿皮绶带系腰。身有四手。左上一手执持莲华。左下一手执持澡罐。右上一手执持数珠。右下一手垂于向下作施无畏。著天妙衣一切严具。以为严身立莲华上。百千光明庄严头冠。并散杂花令有威德。半月璎珞璎珞其身。耳珰臂钏及以手钏。而为庄严作欢喜面。其顶上持阿弥陀佛。造此像已。白月八日十五日。以吉宿日无云无风日。或于春时或当秋时。先于城外净料理地。除去瓦石棘骨恶物。其地平正不高不下。其土白色或有青草。种种花树果木稠林茂盛之处。流泉浴池周遍有处。而作方坛以五色粉布之好画。言五色者。一青二黄三赤四白五浅草色。所谓石灰赤土雌黄金精及以金土。以如是等五色之粉。用严其坛坛作四门。此门则是四吉祥门。又作商迦(此云白螺)及难提迦室哩(二合)伐蹉(西国万字)及满瓶等(以色布地作于瓶形)于坛中心作莲华池。池中具作种种莲华及诸杂鸟鹅雁之类充满其中。于其池中安置尊像(其池亦以彩粉布地)以种种花花鬘末香烧香涂香。及幡幢盖建立坛中。于坛四面各置一瓶。或金或银或铜或瓦。于其瓶中满盛净水。又以种种诸花树枝插于瓶口以缯帛束(以缯帛束瓶中树枝)并一切药宝珠金等盛其瓶内。彩画瓶上极令妙好。又于坛内散种种花及稻谷花。插众花树充满坛中。张于白帐于坛四面。各令一人守护其坛。其持咒者香汤洗浴著新净衣。每日三时受三律仪。于观自在菩萨前献白食供养。所谓乳酪及酥蜜等。烧沉水香檀香酥合龙脑香等烧供养已。持咒之人结加趺坐。作莲华印当心合掌。礼拜一切诸佛菩萨已即当诵咒。可见,在四臂自在观音的仪规中,其中一手执瓶,而所执之瓶,正是澡罐。所以,观音的执瓶,既可以是净瓶,也可以是澡罐。而作为观音化身的僧伽,手持的澡罐,也其实可以是净瓶。只是作为僧伽信仰,作为僧伽艺术图像,他也总得与观音信仰、观音的视觉要素保持一定的区分。哪怕在器具造型上是雷同的,在称呼上也需要显示出仿佛是两种迥然不同器具似的。
同样,《乾隆大藏经大乘五大部外重译经佛说陀罗尼集经十三卷卷三画大般若像法》中,也对如何画大般若菩萨像有详尽的仪规,般若菩萨是十波罗蜜菩萨之一,乃千手观音之眷属:“其菩萨身。除天冠外身长一肘(人一肘如佛一磔手)通身白色面有三眼。似天女相。形貌端正如菩萨形。师子座上结加趺坐。头戴天冠作簸箕光。其耳中着真珠宝珰。于其项下着七宝璎珞。两臂作屈。左臂屈肘侧在胸上。其左手仰五指申展。掌中画作七宝经函。其中具有十二部经。即是般若波罗蜜多藏。右手垂着右膝之上。五指舒展。即是菩萨施无畏手。菩萨身上着罗锦绮。绣作[袖-由+盍]裆。其腰以下着朝霞裙。于上画作黄色花亵。天衣笼络络于两臂。腋间交过出其两头。俱向于上。微微屈曲如飞扬势。其两手腕皆着环钏。菩萨右厢安梵摩天。通身白色耳着宝珰。其项上着七宝璎珞。立[毯-炎+瞿]毹上。右手屈臂向于肩上。手执白拂。左手申臂手执澡罐。其腰以下着朝霞裙。以罗绮锦绣严饰衣服。其梵天身披紫袈裟。顶戴花冠作簸箕光。其手脚腕皆着宝钏。

僧伽观音主题花钱私人藏品
2、澡罐与净瓶佛教本来就是外来的胡教,早期对僧众的用具进行规范和描述的时候,很多都是外来词绘。其中就有一件器具叫做澡罐,所谓澡罐,乃是僧人盛盥漱用水所用之器皿。《杂阿含經卷第二十》对澡罐有一个解读:“澡罐。澡:子皓切,洗手也;罐:古玩切,瓦瓶也”。所以,所谓澡罐,本意就是储存净水用于洗手的瓦瓶。澡罐,亦称澡瓶,又称军持、净瓶。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十五“澡罐”条曰:“盛净水瓶也。”卷四十“军持”条曰:“澡瓶也。”《释氏要览》中说得分明:“净瓶,梵语军迟,此云瓶,常贮水,随身用以净手”。
高丽藏本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二七《明杂诵跋渠法之五》:“若衣、若钵、若小钵、若键镃、若腰带等及诸一切,要使得一物。”卷二八《明杂诵跋渠法之六》:“杂物者,钵、钵支、腰带、刀子、针筒、革屣、盛油革囊、军持、澡瓶,如是比杂物施,现前僧应得,是名杂物。”卷三一《明杂诵跋渠法之九》:“檀越施僧床褥、俱襵、氍㲣、枕㲲、腰带、刀子、伞盖、扇、革屣、针筒、剪爪刀、澡罐,是中床褥、俱襵、枕氍㲣如是重物,应入四方僧,其余轻物应分。”可见澡罐作为佛家日常用具十分普遍,同时,也有军持与澡瓶并列的,说明两者或有差异,或有演变。
《乾隆大藏经 受用三水要行法一卷 受用三水要行法》中,对僧众的用水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规范:准依圣教。及西方现今众生所用之水。有其三别。一时水。二非时水。三触用水。言时水者。谓是沙弥俗人。自手滤漉观知无虫。午前任受而饮。若大僧手触盆罗及杓水即不堪入口。而况食用。有恶触故即如僧家常用之水。大僧岂可得触。虽大僧不触。于午后时不合饮用。然水体无触。已是俗人等触。带于染腻非全极净。是故须受。二非时净水者。谓大苾刍及沙弥等用意之人。并须澡豆及上屑等。连腕四指。咸须净洗无有垢腻。瓦盆及罗并须新净。不与垢腻相染者方得。罗滤此水。皆用铜碗铜杓。灰揩去腻始得取水。若无此等可求。必有染木之器。不曾与触腻相染。每日净洗尘垢不停者。通用亦得。若常用水可贮在净瓶。净瓶须是瓦。非铜澡罐。由其瓶内有铜青不净不得灰揩故。拔出铜钗揩拭。即知净秽。然铜以灰揩为净。圣教亲说。若澡豆洗。但去食腻。铜垢不除。可取铜匙灰揩。足为目验。其瓦瓶水尽。每须洗濯中间方盛新水。然五天之地。无将铜瓶为净瓶者。一为垢生带触。二为铜腥损人。此之净水时与非时。任情取饮。是佛别开。以其净故。更不劳受。若苾刍在非时中。煎药煮茶作蜜浆等皆用此水。不得用前时水。以有过故。然用枪杓碗器。皆须离食染。并悉灰揩方合煮物。其净水盆瓶。宜于净处安置。盆须净物覆盖。瓶即置在竹笼。不得辄令触。欲用水时先净洗手。或用干牛粪。净揩手已。无腻方触。或以净绢布及叶。用替瓶咽。然后方捉。律云。除水及杨枝者。谓此清净之水。非是余二。杨枝若是新条湿者。应须火净受而嚼。故知不可直执戒文。凡欲以水入口。若饮若漱时与非时。皆须澡豆净洗手洗净两唇。漱口再三方合饮水。吃食亦然。又中食了时。若恐净瓶水少。须令俗人授前时水。嚼齿木澡漱已。然口津未得辄咽。要须以此净水三漱口已。方是清净得咽口津。目见西方南海僧众共行此法又此方古德律师有知斯事。然行之者希。若不如是。余腻不除咽咽得罪。亦斋不成。三触用水者。但使无虫。不论净触即得受用。谓添触瓶向大小便处。及洗手足。更余用不得辄将入口。况食用耶。此等三水观知无虫。乃至明相未出已来。皆随事得用。明相既出即便不合无问多少。乃至瓶内一抄盆中一合。悉须铜盏。明目观察。若无虫者。虽经多日任用无犯。西方僧徒及俗人五戒以为急。若外方客僧不解此水净触法者。无容入寺。又复西方寺法。若见有僧将净瓶上厕饮触瓶水者。以为灭法。即摈出寺。以此言之。冀诸行人。共为存护。令佛法久住。若能依教行者。即是与佛在世无有异也。又旧律十诵五十九云。有净澡罐厕澡罐。四十一云。有净水瓶常水瓶。又新译有部律文。净瓶触器极分明。此并金口亲言。非是人造。宁容唯一铜瓶不分净触。虽同告语不齿在心。岂可以习俗生常故违圣教。准如此理。诸寺房中及行方等处。所有用水非常狼藉。或大盆贮。或盆子盛安瓶内。皆不合用。以是大僧手触不好罗滤。经宿不观。停贮多时定有生命。设使无虫。当第三水饮用得罪。谓由盆罗及杓是不净手触有不净尘故。又如寻常用水铜瓶。若自取饮者。以其不净不受而饮。有不受罪。若中前触至过午饮。增触罪。若今日触明日饮。有宿触罪。不受而捉。有恶触罪。不净洗手。复有污手捉饮器罪。不净洗唇口饮水。有不净罪。此之六罪。各有方便成十二罪。皆有不敬圣教罪。此有因本。......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佛家对僧众生活的清洁有严格的要求:1、平时喝水所储水的净瓶质地须选择瓦瓶,不用铜瓶,防止生锈与铜腥味。2、净瓶之水供饮用,触瓶水洗手足。更有说,净瓶之水洗净手,触瓶之水洗污手。可见,净瓶是储存净水的容器,质地为瓦瓶。3、佛经中军持之所以与澡罐并列,也许在该语态中,澡罐作为饮水之器,而军持作为洗手之器的分别。也就是净水瓶与常水瓶的区别。由此我们可以大体知道,佛家实用意义上的净瓶,大致是饮用纯净水的容器,而澡罐澡瓶,大致是洗手用的随身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