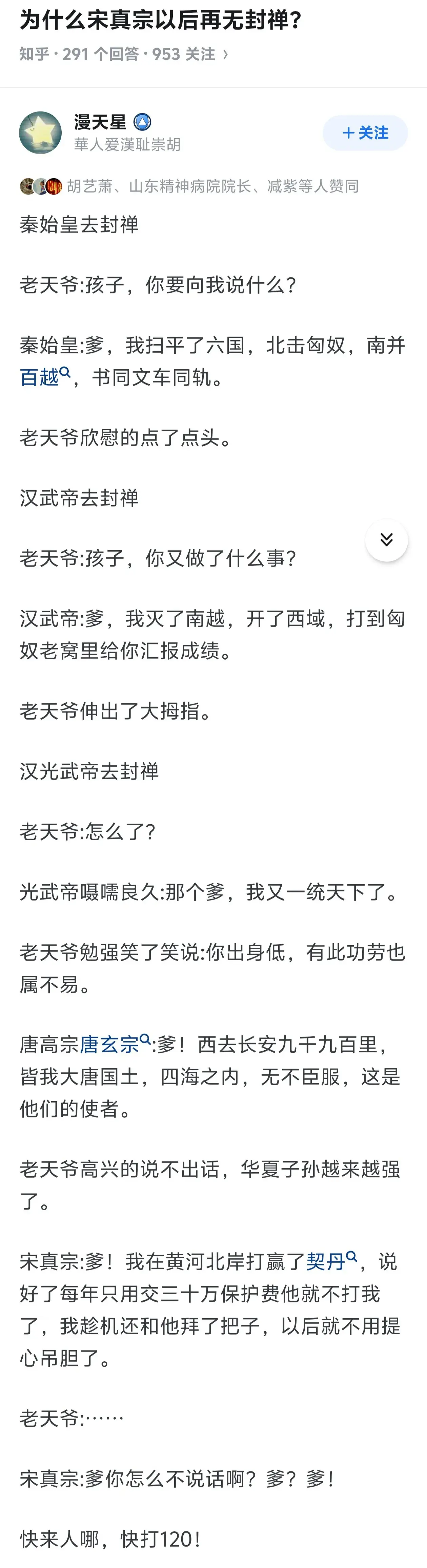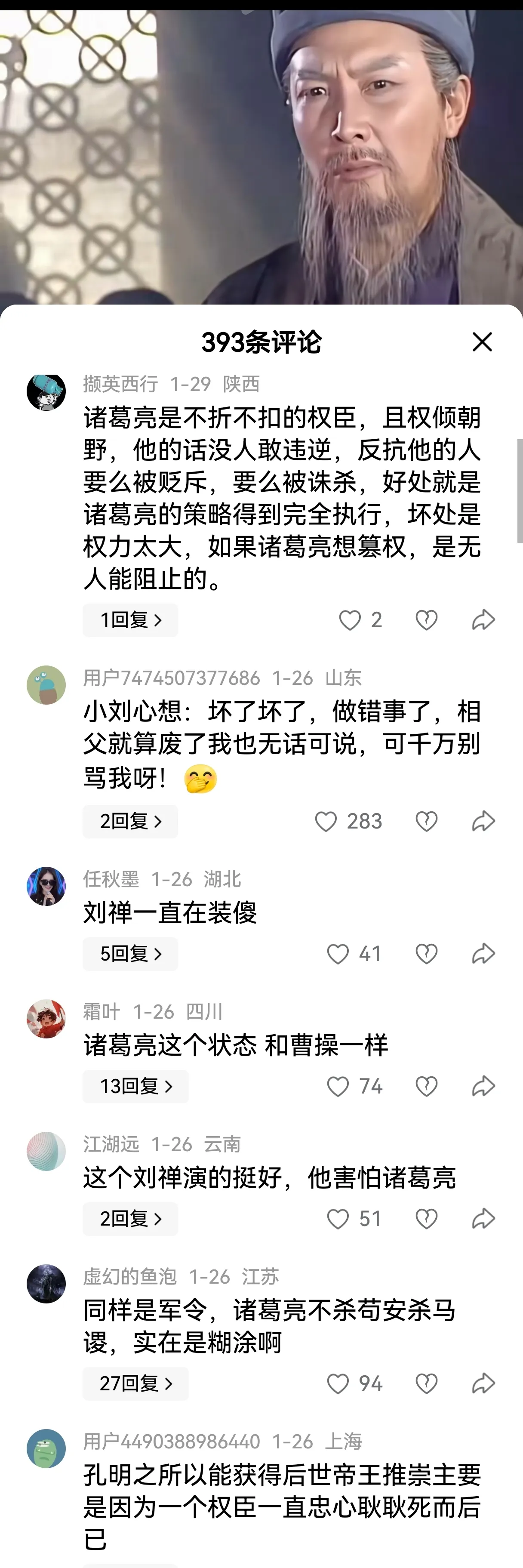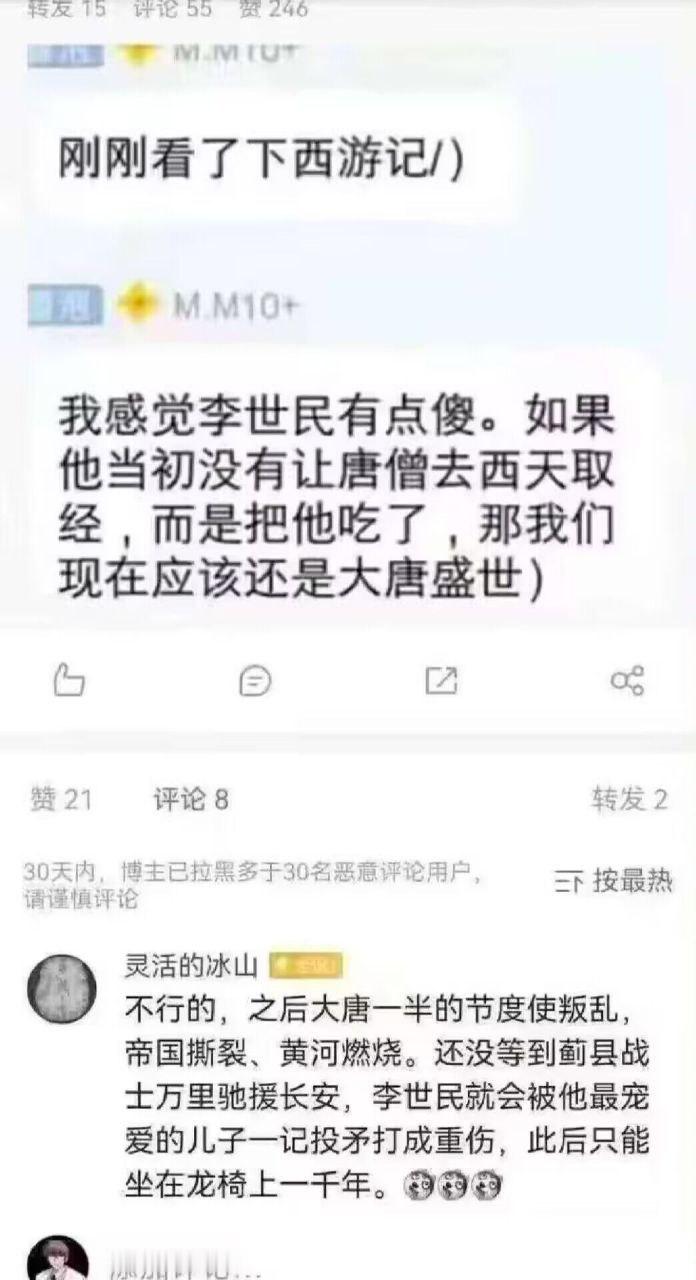公元721年,宰相姚崇患病,命不久矣。咽气前,他掐着长子的手,含泪说:“我走后,咱家会被灭族!有1件事,你须谨记,听我安排。” 开元九年深秋的长安城飘着细雨,宰相姚崇躺在病榻上,蜡黄的脸贴着冰凉的玉枕。窗外银杏叶簌簌飘落的声音,让他想起四十年前初入政坛时,在洛阳皇城踩过的满地金黄。
三朝老臣的手紧紧攥着长子姚彝的衣袖,指甲在锦缎上掐出十道深痕。
"等我这把老骨头入了土,张说那厮必来寻仇。"姚崇喉咙里像塞着团棉花,每个字都带着血沫子,"灵堂里摆上我收藏的吴道子《天王送子图》,再把阎立本那幅《历代帝王像》挂在最显眼处。"
他说着剧烈咳嗽起来,侍妾慌忙递上的丝帕转眼染成猩红。姚彝扶着父亲骨瘦如柴的后背,感觉掌心硌着嶙峋的脊梁骨。
停灵第七日,新任中书令张说的车驾果然停在姚府门前。这位以文采著称的权臣跨过门槛时,官靴特意在青石台阶上蹭了三下,姚崇生前最厌恶别人穿着脏鞋进他书房。
可当他的目光扫过灵堂,脚步突然像被钉住了。二十年前姚崇平定契丹叛乱时,先帝赏赐的羊脂玉镇纸正在烛火下泛着温润的光,旁边搁着太宗皇帝御赐的鎏金香炉,连插着的线香都是宫里特供的龙涎香。
姚彝捧着孝布跪在棺椁旁,看着张说喉结上下滚动。这位父亲的老对头此刻正盯着《天王送子图》上吴道子的落款,手指无意识地在袖子里捻动,活像见了荤腥的狸猫。
姚彝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张伯高爱古玩胜过性命,你只管把东西往他眼皮底下堆。"
"先父临终念叨,说满朝文武唯有张相文采可追司马相如。"姚彝的声音适时响起,惊得张说手里的三炷香差点掉在蒲团上。
灵堂里檀香混着潮湿的霉味,熏得人太阳穴发胀。张说转头看见姚家三兄弟齐刷刷跪成一排,忽然觉得这些往日里鼻孔朝天的贵公子,此刻倒像极了坊市间捧着宝贝求人鉴定的商贾。
七日后,张说府上送来份洒金笺。姚彝展开时手抖得厉害,生怕墨迹未干的墓志铭上藏着什么诛心之语。
谁知开篇就是"姚公崇,字元之,陕州人也。少倜傥,尚气节,长乃好学,下笔成章......"洋洋三千言写得情真意切,连姚崇年轻时在兵部当差,寒冬腊月给戍边将士送棉衣的旧事都翻了出来。
这文章递到唐玄宗案头时,正逢岭南进贡的荔枝送到。皇帝嚼着清甜的果肉,看到"开元之初,政归台阁,天子垂拱,九译来朝"这句,朱笔在奏折上点了又点。
次日早朝,张说听着内侍当众诵读自己写的墓志铭,后槽牙咬得发酸,那字字句句如今都成了烙在姚家身上的护身符。
姚崇下葬那日,终南山飘了场太阳雨。新立的墓碑淋得水亮,张说站在送葬队伍最末尾,官袍下摆溅满泥点。
他望着青石板上自己亲笔写的"持衡守正,开济为先",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在政事堂和姚崇吵架,老宰相气得摔了茶盏,碎瓷片在孔雀石地砖上蹦得老高。
如今想来,那会姚崇咳疾已重,捂着嘴的帕子上怕是早见了红。
三个月后,有御史弹劾姚家侵占民田。张说在紫宸殿听着同僚们议论,袖袋里还揣着姚彝前日送来的王羲之字帖。
等皇帝眼神扫过来,他脱口而出的竟是:"姚相当年整顿吏治,最恨贪墨之事,其子断不会如此。"话说出口才惊觉失言,抬头正撞见皇帝似笑非笑的表情。
这场风波最终雷声大雨点小,姚家退还了三十亩地,事情便揭过不提。
倒是张说某日下朝,看见姚彝捧着个紫檀木匣等在宫门外。匣子里装着吴道子的真迹,姚彝说这是替亡父谢他保全家族之恩。
张说接过木匣时,忽然觉得长安城的秋风格外刺骨,吹得人眼眶发涩。
姚崇的算计终究成了现实,往后二十年,每逢清明总有言官想翻旧账,可只要拿出当年御笔亲题的墓志铭,再大的风波也会渐渐平息。
张说晚年写《姚文献公神道碑》时,添了句"智者虑远,达者守常",笔尖在"虑远"二字上重重顿了两下,墨迹晕开像滴陈年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