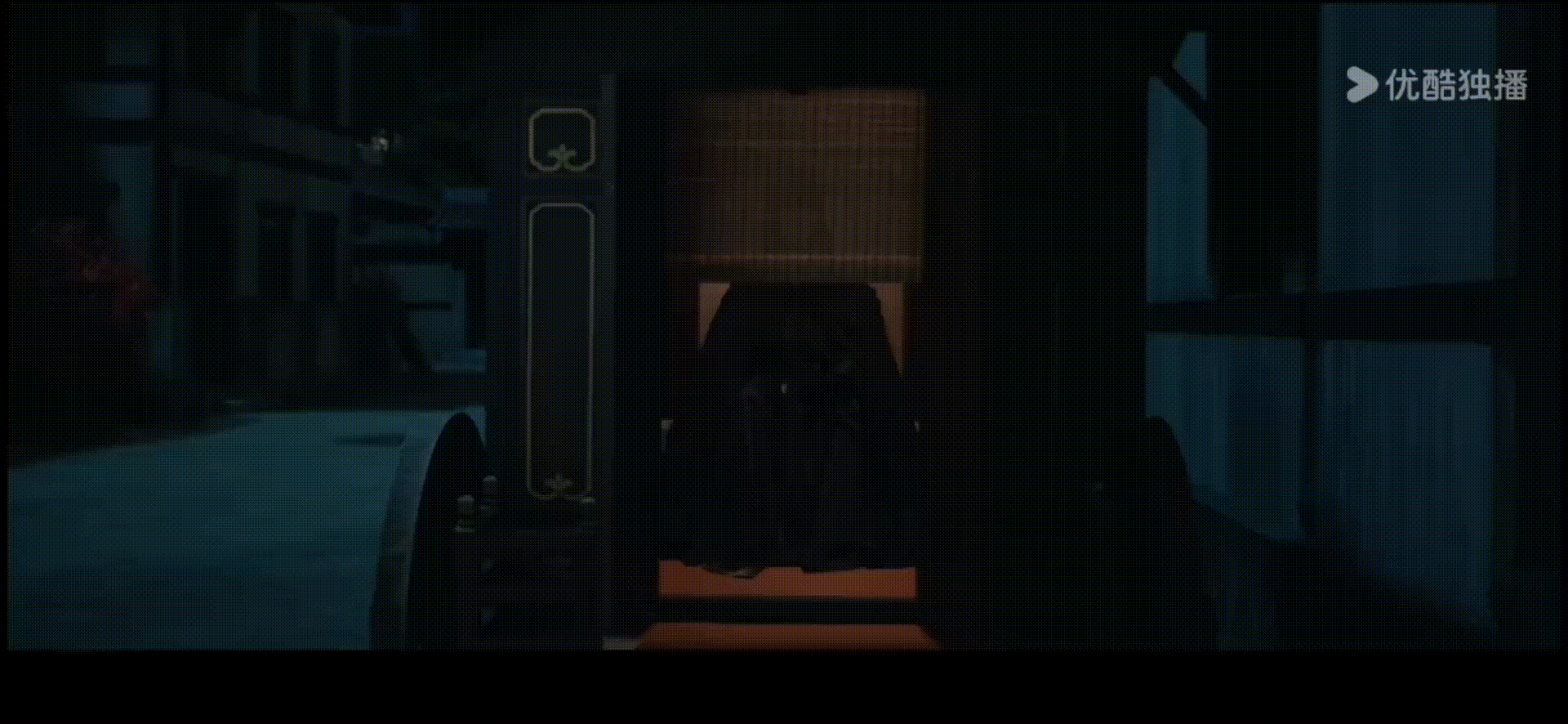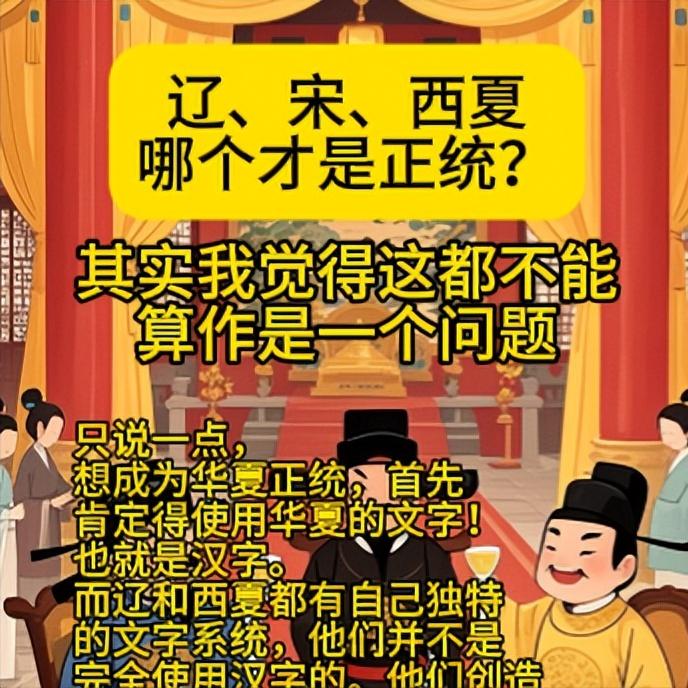1929年年初,东北大帅张学良下了一道惊天命令,在奉天帅府老虎厅,当场枪决了杨宇霆和常荫槐,这两人不是普通军官,而是他多年的谋士、旧部,一句话没说完,枪响了,两具尸体倒地,军中哗然,张学良站在原地,脸色铁青,没有回头。
东北易帜之后,局势越来越复杂,表面看是张学良当家,其实不少人心里并不服,尤其是杨宇霆。
他是老资格,早年随张作霖南征北战,打出一片天地,奉系军阀里,能动脑子的没几个,杨就是其中之一,可他不懂收敛,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
张学良那年才二十七,虽然被称为“少帅”,军中不少老兵都在观望,看看这年轻人能撑多久。
杨宇霆看他年轻,经常当众喊“小六子”,说他不懂军事,决定不了事。
有一次会议上,当着一群将领的面,杨直接拍桌子说:“你太嫩,不行!”张学良脸挂不住,转身走了。
这种事情多了,张学良压着火,没立刻翻脸,他不是不知道杨宇霆背后跟蒋介石、白崇禧联系,私底下还绕过他订购日本的枪。
更过分的是,杨自己成立“山林警备队”,军饷也不报备,搞得像另立山头。
东北的军队像一盘散沙,很多军官看杨的脸色行事,张学良心里清楚,再这么下去,位置保不住。
真正让张下定决心的,是一场寿宴。
1929年,杨宇霆的父亲大寿,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几乎都去了,张学良带着厚礼亲自到场,按照辈分和面子,这场合他应该是主角之一。
可场子里冷得很,杨家的人没几个人起身,杨自己出来打了个哈欠,说了句“先歇会”,转身走了。
回家的路上,于凤至一肚子火,质问张学良:“你哪里像个东北的主人?那架势倒像是他做大帅了。”
她不是外人,是张学良的妻子,虽是政治婚姻,可聪明能干,一直跟张打理军政大事。
她这一问,戳到了张学良的软肋,男人脸最重要,尤其是这种身处风口浪尖的人物,那晚,张学良一夜没睡。
几天后,杨宇霆拿着文件来逼张学良签字,是关于设立铁路督办公署的,这文件一旦落笔,张手里的交通、军工系统就都归了杨管。
张学良接过笔,笑着说:“这事大,得商量。”实际上,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当晚,他拿出一枚银元,丢在桌上,正面朝上,他又丢一次,还是正面,第三次,还是一样。
旁边的于凤至当时就哭了:“你真要杀人?”张没说话,这个细节后来在张学良晚年口述中也被提起。
他说:“银元三次都一样,我就觉得该动手了。”其实银元只是借口,该做的决定早就做了。
张学良让亲信高纪毅动手,1929年1月10日,老虎厅安排了“军事会议”,杨宇霆和常荫槐如约而至。
一进门,门一关,枪一响,两人倒地,军中瞬间传遍了消息,有人害怕,有人拍手称快,张学良对外发布命令,说二人“阴谋叛乱,阻碍新政”,必须清除。
事后处理也算周全,张学良私下安抚了杨宇霆家属,送上抚恤金,还说不会追查其他相关人员。
这招稳住了人心,没人敢再动,东北易帜正式完成,蒋介石也松了口气,东北终于听话了。
可后患也跟着来了,东北军的元老派心凉了,开始各自打算,热河守将汤玉麟干脆不交权,说是“避嫌”,其实是怕步杨的后尘。
日军那边更是高兴。之前他们对杨宇霆是忌惮的,杨的强硬立场多次阻止日方渗透东北铁路。
一死,东北防线顿时松动,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轻而易举占了东北,张学良在回忆时说过:“杨若在,未必如此。”
张学良不是没后悔,他晚年在夏威夷养病时,接受采访,说起当年的事,一直摇头。
他说,杨宇霆是个能人,杀他不是怕,而是时势所逼,还说:“银元占卜其实是懦弱,不敢自己拍板。”
张学良一直被关到1988年,晚年在美国接受过多次访谈,他反复提到一件事,就是杨死后,他的身边没有再出现一个能拍桌子提意见的人。
中日关系恶化,东北军混乱,西安事变被软禁……一步步都像是连锁反应,他曾感叹:“如果当初我能再多考虑几天,也许结局不一样。”
这件事在历史上争议不小,有人说张学良果断,有魄力;也有人说他草菅人命,心狠手辣。
但有一点没人否认那是他人生最关键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