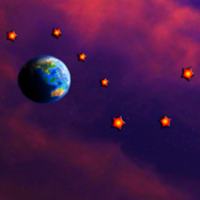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曹昱

距离安徽凤阳县城南25公里,藏身于韭山国家森林公园深处,有一处古刹,名叫禅窟寺。周日的下午,由当地院校的朋友做向导,我们乘车从蚌埠出发,一路向南,寻觅这个深山古寺。
安徽与河南一样,同属中原文化大省,数千年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令我这末学望而敬畏,不敢造次。就拿这凤阳来说,也有着太多的人文、自然旅游资源,明皇陵、明中都,花鼓灯等等都已经广为世人所知。因为此行来蚌埠是短暂停留,不能有太多时间尽情领略当地的人文,途经明皇陵的时候,也只是站在门外看了看。我想,以比较短的时间,领略一处相对完整的文化碎片,也不至于意犹未尽,其它的,只好留给以后有缘再来时细细品味。
车驶入禅窟寺景区,过一个古色古香的石牌坊,行不多远,前面是一处水泥修饰制作的景观大门。那人工修饰的如同卡通画片的大门,与四周沉寂的大山、绿树衬托得格外醒目,但是,又觉得很不协调。更让我奇怪的是,过大门的道路两边耸立着12根生肖石柱,搞不清楚这些生肖石柱与这里的景观有什么联系。
院校的朋友请来一位小姑娘给我们当导游。一进门,看见的是一座苗寨,导游告诉我们说,里面有歌舞表演。我倒觉得这里出现这样的内容有些唐突,容易冲淡此行的主题。我们绕过苗寨直奔山坳。来到一处簇簇翠竹掩映的石级前,手轻轻撩拨开凌乱的竹叶,逐石阶而上,走上一个开阔的平台,景色已经与此前所见迥异,地面的石板虽然凌乱却也平整,看似随意却又错落有致的树木,伸向苍穹的枝干苍劲有力,已是山阴,再置身于这样的树林之内,非“深”和“幽”无以形容。
再上一道台阶,迎面又是一个宽阔的平台,大理石板铺陈,显然刚铺设不久,还没有留下岁月的划痕。平台的中间是三层黑色吊脚铁香炉,没有香火缭绕,香炉下散着一堆鞭炮的碎屑,后面再上六层石阶就是禅窟寺的庙门。一位身着灰色僧袍的人正坐在那里与一商客下象棋。庙门的两侧各摆放着一盆枝叶茂盛的铁树。刚整修过的庙宇,青砖墙体,砖与砖之间的白灰平整清晰,高四五米,橘红色琉璃瓦顶,殿角重檐,顶上平脊。庙门两侧是斑驳的黄色围墙。对古代建筑,我是门外汉,所以,也看不出有什么别致的地方。不知道整修前的庙宇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铁香炉正对着弯月中门,两边各一个弯月侧门,门前各置一对石鼓,中门之上白底黑字书“禅窟寺”三字,仔细看后面的题款:“苏轼书”。
我翻过苏大学士的文集,他对寺庙情有独钟,祖国大江南北大大小小诸多的寺庙似乎都留下了他的痕迹,即使这里如此偏僻的地方,仍能寻到他的影子,真个是做官、为文、游览都不耽误。

导游小姐告诉我们,禅窟寺名字的由来,有一段美丽的故事。相传,当年西王母赐给汉武帝蟠桃时,途经此处撒下遗种,寺成之后,因满山桃花,故取名桃花寺。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寺名屡屡更换。隋代,钟离刺史游览至此,看见“僧方唐持率甚严,每行路有虎随之”,寺名改为虎窟寺。至唐时,因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为了避讳,取此地所产的一种只有指甲大小的蝉,更名为蝉窟寺。到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慕名来游,因为苏东坡是居士,取在洞旁参禅的意思,把那个“蝉”改成了“禅”字,挥笔改名为禅窟寺,延用至今。
门前一侧有两座石碑,走过去仔细看来,是清朝的碑刻,上面写着禅窟寺的来历,与导游小姐说的大致相当。据碑文记载,该寺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纪的汉武帝年间。这样计算,禅窟寺比有那个有中华第一古寺美名的洛阳白马寺还早了近200年,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绝对是深山古刹。只是,从上面的记载看,两千多年来,这里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不比那些历经数度战乱和毁誉的庙宇,就那么平静地过来了。如是,这个寺庙的规模、结构到几个大殿的基本构件,现在的人对于庙宇重新修缮时,只要没有推倒重来,应当保存了汉武帝年间的历史痕迹。这应当是国内许多寺庙难以相比又稀罕一见的妙处。只是,我这俗人恐怕难以识别出来。
进入庙门,院子不大,左右两边禅房,跨上院子中间的小石桥,绕过中轴线上的高脚香炉,便来到了“大雄宝殿”,殿内释迦牟尼端立正中,十八罗汉分列两厢,几个僧人坐于蒲团之上。因为只有我们这几位游人,这里显得格外寂静。
出“大雄宝殿”, 就来到了寺院的后面。沿着导游指引的路线,继续前行几步,我们就来到了一面峭壁之下。峭壁一侧刻着“玉蟹泉”三字。据说,因为这里盛产白蟹,苏东坡来到这里,看到这些白蟹,就写下了这三个字。我们走上近前,“玉蟹泉”的泉水来自它上方的峭壁底部的一个浑圆的大山洞,泉水之中果真能见到几只白色的小蟹,静静地卧在细细的沙石泉底,手指轻轻搅动水面,那几只小蟹便胡乱躲藏起来。
回过头,在峭壁之下走过一段弯曲狭窄的小路,就来到了禅窟洞。禅窟洞分水旱二洞,水洞长年水流不止,且水质清冽。旱洞是禅窟祖师猛修身养性、传经布道的佛窟。
我们跟着导游,沿着向下延伸的石阶,弯腰曲背走下去。“禅窟洞”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溶洞,据说有6000多米长,原是禅窟寺和尚坐禅,修身养性的地方。

洞里很潮湿,摸一下石壁可以沾满手的水珠,时而还能看到惊飞的蝙蝠,虽然在石壁上安装了灯光,但是,这些七彩的灯光多为装饰之用,能见度仍然有限。也许,这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洞里有许多鬼斧神工的钟乳石,形态各异,灯光大都打在这些钟乳石上,而导游则指着这一个个钟乳石,开始一段段讲起佛陀降生、佛陀出家、悟道成佛、初转法轮、普度众生的故事。故事的确是佛教里的经典,但是,导游却把一个个钟乳石演绎到这个故事里,感觉实在牵强。因为,这些石头虽然有的的确像人,有的需要提示才能觉得有些相像,但是更多的在我看来根本挨不着边际。虽说这个寺庙敬的是释迦牟尼佛,但是,这里既无佛祖之舍利,也非名师大寺之显赫名声,更没有蕴藏史册的佛家典故,把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硬往佛祖身上拉扯,不仅有些荒唐,而且也有对佛祖大不敬之嫌。
听几句导游胡乱联系的讲解,我暗觉好笑,便自顾向前走,蹒跚着跨过脚下的小溪流,走过崎岖不平的狭窄通道,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惊讶地发现,石壁的一侧,雕刻着三十多幅佛祖画像和许多的诗句,佛像或坐或卧,或喜或怒,或静或动,线条流畅,姿态万千。我取下眼镜走近了观瞧,雕刻的痕迹并不深,刻槽里描上红色的漆料,画像里有五祖弘忍、六祖慧能、还有神秀等等。我问导游,这些画像和诗句是现代人刻的还是古人留下来的?导游小姐笑而不答。我说,如果是现在刻上的,很有创意,如果是古人留来的,那可有说法了,很值得好好研究研究。我知道,为了争得衣钵,神秀追杀慧能,两人应该不相融的。画像把他俩排在前后,不知这种排序是否有什么讲究。
导游小姐介绍此地景观的时候,我还注意到,她提到禅窟寺景区二十余处大小景点中有一处名叫“顿悟亭”。据我所知,“顿悟”是禅宗有别于其他佛教流派的重要标志,也是其达到“涅槃”境界的不二法门。当年,五祖弘忍传衣钵留下了神秀立“渐修”之北宗和慧能立“顿悟”之南宗。慧能讲求唯心净土,不需出世求佛,不必出家修行,将传统的以佛为中心的佛教改造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佛教,以“众生是佛”,“顿悟”为成佛之道,结果,慧能宗风独尊于天下,神秀北宗则门庭寂寞,传不数代即衰亡。我想,既然这里有“顿悟亭”,应该是有些说法的,最起码应该有一个求佛之人在此期望过或经历了“顿悟”的故事。只是,给我们做导游的小姑娘实在说不出个所以然,那个景点也尚在建设,心里颇感遗憾。
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段石阶前,岣着头向上攀爬了好长一段,眼前豁然明亮,不知不觉间,我们已经走出了溶洞,向四周看去,我们已经置身于山顶。
下山的时候,导游又引领我们来到禅窟寺后山的狼巷迷谷,这里因谷深奇险、常有野狼出没而得名。置身其中,岔口密布,峡谷狭窄,且两边岩壁如刀削一般,令人胆战心惊,时而侧步挪身,时而原地回转,莫名方向,的确称得上巧夺天工的造化。直到上车踏上归途,我仍为刚才的思绪不能释怀。我总觉得这是一个待以深入挖掘历史的寺庙,应该找机会看一看先后辖域这里的凤阳和怀远的县志,兴许,那里会有所发现。一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寺庙,不会如此简单地存在着。既然存在,就应当找到它深藏的文化价值,这样才能物有所值,得以化人。

☆作者简介:曹昱,河南许昌人,出版著作两部。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