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一张经方是需要时间的,随着学习的深入和实践的增加,认识会越来越清晰。
娄绍昆老先生在《讲康治本伤寒论》中提到大塚敬节使用半夏泻心汤的经历,引人深思。
敬节用三黄泻心汤消除了一壮汉的烧心、胸部憋闷、入睡困难,患者很高兴,介绍弟弟来诊。敬节根据弟弟心窝部痞塞感和腹泻,投半夏泻心汤7付,岂料患者再未复诊,后来问哥哥,说是弟弟吃了半夏泻心汤,出现严重腹泻,一天上六七次厕所,无法工作,再也不想吃中药了。敬节说半夏泻心汤里没有泻药,反而能止泻,但患者已不愿再试。很长一段时间,大塚敬节先生都把服用半夏泻心汤后引起腹泻当成“瞑眩反应”,排邪反应。
直至他自己的妻子便秘,平素用黄解丸(大黄、黄芩、黄连、黄柏、栀子)一吃就灵,这次怎么吃也不管用,他因此建议妻子试试生姜泻心汤,因为好多患者排便不舒畅,吃了半夏泻心汤感到很舒服,加之好几例患者吃完后腹泻而无法解释。结果他妻子吃一帖,就爽快地排出大便,胃部也很舒适。大塚敬节回想起之前那个吃了半夏泻心汤一天上六七次厕所的患者,猛然发觉不是“瞑眩反应”,而可能是辨证错了,应是理中汤证(患者不到50Kg)。
我想到半月前,我因自己服半夏泻心汤改善了肠胃和入睡慢而狂喜,甚爱此方,给一个易腹泻的患者投用,再未复诊,我实在忍不住打过去电话,患者说根本不管用,又找别的医生治疗后腹泻才改善,我说能否把药方告诉我,以备学习,患者不耐烦地说,在老家找的医生,没见过面,不给药方,只配药!我后来仔细一想,患者应属理中汤之类……
娄绍昆老先生在他80多万字的遗作《讲康治本伤寒论》中反复强调“虚实方向感”是辨证首要解决的问题。比如一个患者腹泻,体重小,食欲不振,体质差,就提示“虚”,首先就不应考虑半夏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的“下利”,应该大多是“食积”导致的,吃太多了,肥胖了,排不出去了,老要排,就是我这种情况,而不是,瘦瘦的,不能多吃,稍微多吃就要泻,必须分清楚的!或问,半夏泻心汤里为何要用草、枣、人参?因实致虚,生病起于过用,长期多食过食,脾胃气虚是必然结果,但如果因一个多食易饥的大胖子便“溏”而用纯粹健脾补气的,导致他们食欲更加旺盛,那岂不是糊涂医生吗?
学经方,学的是“理”,仲圣看似不言“理”,理都在其中。把人的吃喝拉撒睡研究透彻,再厘清精神疾患导致的躯体障碍,很多病都有办法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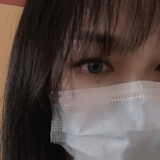
像中医致敬
瞑眩反应是不是用方不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