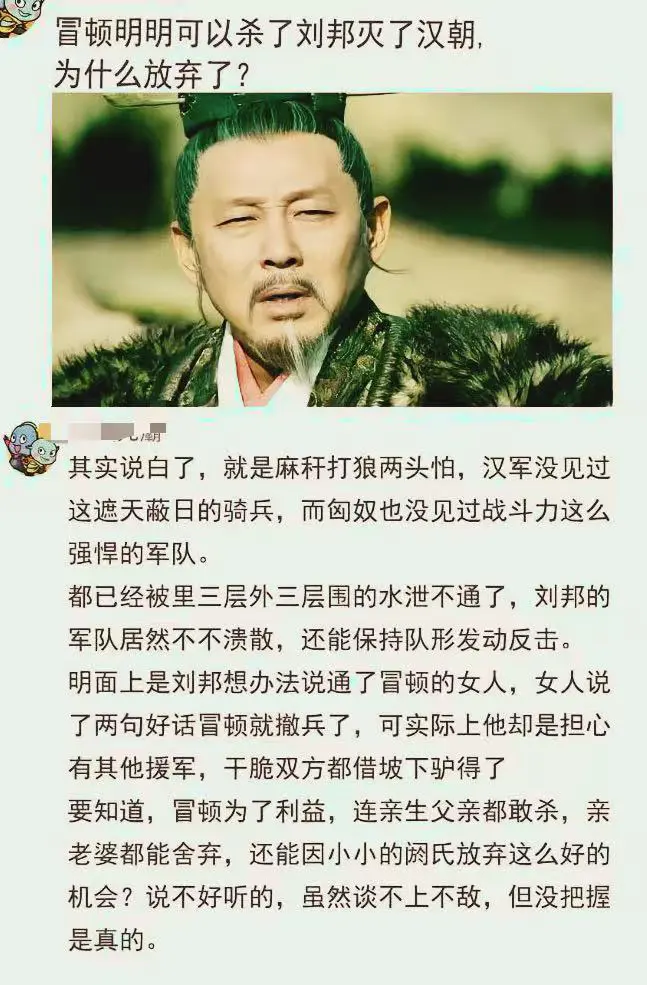吕后刚刚咽气没几天,长安城里杀气腾腾,宫门紧闭,禁军换防频繁,城中谣言四起:吕产、吕禄这对外戚兄弟,要挟太后遗命,准备自立为王。 陈平、周勃表面上镇定如常,暗地里却已经召集旧部、联络宗室,准备动手,谁都知道,要是让吕家得逞,白马之盟就彻底废了,刘家的天下也就没了。 当年在白马驿,刘邦召集一众功臣饮血盟誓,说非刘氏不得为王,非战功不得封侯。 大家把马杀了,血灌进鼎里,一人一口饮下,这事传出去,听起来挺神圣,像是定下了一个天大的规矩。 可实际上,那就是个拿来稳住人心、收买功臣的说辞,刘邦不是傻子,他早看明白,这群跟着他打天下的人,心里都不甘心只当个陪衬,他想让江山传给儿子,就得先稳住这些兄弟。 但这盟约压根就没个约束机制,说白了,谁真守着它谁吃亏,吕后就是个例子。 她身为皇后,掌权多年,想让吕氏家族分享点权力,本也算合情合理。 可功臣集团不干。陈平和周勃都是当年盟约的见证人,他们不说是为了刘家江山,而是说吕家干政坏了规矩。 他们不是真的在乎什么刘氏天下,他们是在乎自己的地位。 刘邦死后,吕后开始一步步把持朝政,她先封吕台为将军,又让吕产当了相国。 原来刘邦立下的制度,功臣为辅、皇室为主,一点点被瓦解,吕家不姓刘,这让很多人心里打鼓,尤其是那些靠着刘邦打天下、指望自家子孙能世袭的老臣们。 更关键的是,吕后掌权后,对外显示尊刘,但实则大权独揽,她先扶持年幼的刘盈登基,掌控朝政;刘盈死后,又立年仅八岁的刘恭为帝,自己继续以太后名义执政。 吕氏外戚趁机全面进入朝堂,吕禄掌兵,吕产为相,几乎控制了整个国家机器。 陈平、周勃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早就看出吕氏一家不是来“辅佐”的,是来“篡权”的,他们表面上听命于太后,暗地里却保存兵力。 吕后死后不到几日,吕氏想效仿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立为王。 陈平一纸密令,调动禁军,周勃率兵入宫,一举拿下吕氏兄弟,整个诛吕过程不到三天,干净利落。 这时候,白马之盟又被拿出来说事,陈平站在太庙前对百官说: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捍卫白马之盟。 可那时刘盈早死,刘恭小得说不出话,江山究竟归谁,大家心里都清楚,盟约成了借口,权力才是根本。 追溯当年,刘邦刚灭项羽那会儿,整个国家乱成一锅粥,他手下有韩信、彭越、英布这些异姓王,权力大得惊人。 刘邦心里不踏实,开始一个个收拾,韩信被囚长乐宫,彭越被腰斩,英布兵败被杀,这些人都是白马盟中的关键角色,但照杀不误。 刘邦不是不念旧情,是他明白江山归谁不是靠誓言,是靠拳头。 他后来分封了一批同姓亲王,比如齐王刘肥、代王刘仲,说是为了制衡地方,其实是打压功臣、防止异姓坐大。 这一招确实缓了一时,但也埋下祸根,“七国之乱”时,这些被分封出去的刘氏子孙反而成了中央的心病。 功臣集团也好不到哪去,萧何、曹参、周勃这些人虽然是刘邦信得过的老人,但他们的权力全靠皇帝赏赐。 一旦天子年幼,或者外戚掌权,他们这些人就容易被边缘化,所以,当吕后一步步蚕食权力时,他们一开始能忍就忍,直到忍无可忍。 吕氏被诛后,宗室拥立刘恒为帝,即后来的汉文帝,刘恒一上位就开始清理吕氏残余势力,同时也悄悄削减功臣的权力。 他没有忘记白马之盟,但他也知道,这种东西,说说就好,真当回事,只会束手束脚。 白马之盟从一开始就是个工具,既不是法律,也不是制度,更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 它的目的就是让一群人相信他们能分一杯羹,可只要有利益冲突,就没人再提什么盟誓。 比如东汉末年,曹操打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旗号,说自己绝不篡位,结果他儿子曹丕照样废了汉献帝。 白马之盟的下场,早就注定,它不是倒在敌人的剑下,而是倒在自己人的手里,谁手握兵权,谁就能解释盟约。 陈平说诛吕是为了刘家,那吕产也可以说自己是替太后守规矩,到底谁有理,不是史书说了算,是谁赢了说了算。 参考资料: 《资治通鉴》,司马光撰,中华书局,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