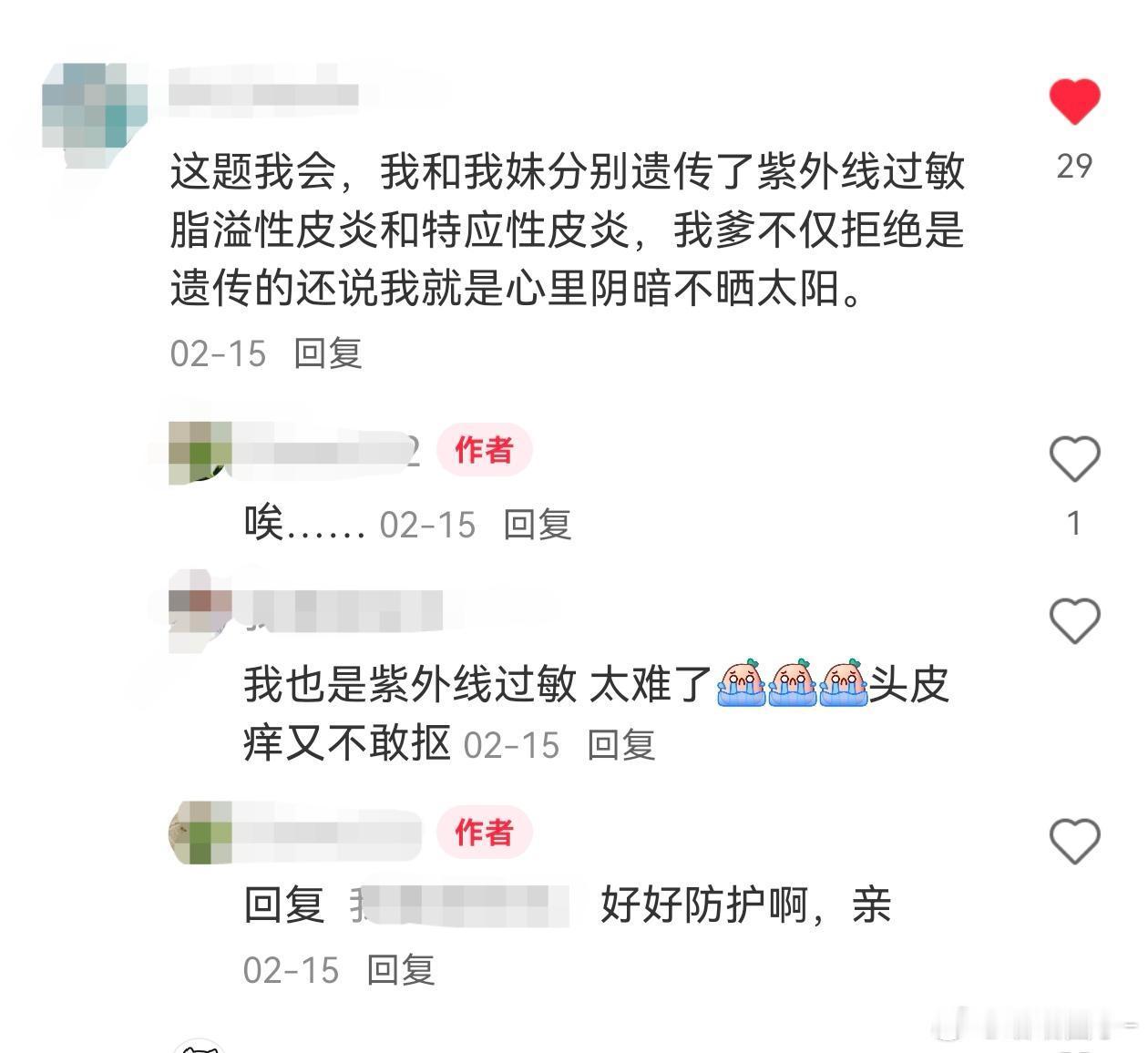潮水漫过天穹时,我把自己揉碎成千万片粼光。骨骼化作珊瑚虫的巢穴,血液与盐粒共振出深蓝的潮歌,皮肤一寸寸剥落成漂浮的月光。下沉是另一种飞翔--鳃裂在颈侧绽放成幽蓝的玫瑰,发丝生长出与暗流缠绵的藻荇,瞳孔里游动着磷虾般闪烁的孤独。
十二月的暖流裹挟着旧日呢喃。鹦鹉螺的螺旋走廊里,回荡着你用黄昏卷成的烟圈。鮟鱇鱼提灯照见岩缝深处,我们曾用叹息豢养的透明水母,此刻正吞吐着被泡软的誓言。暗礁上的藤壶忽然开裂,涌出大段褪色的对白,海葵立刻伸出触手将残章缝补成虹彩的茧。
三千米下的永夜是液态的琥珀。巨乌贼用墨汁拓印你留在玻璃杯沿的唇纹,管虫在热泉口用硫化物结晶出你转身时的弧度。我跪坐在热液喷口的祭坛前,看古菌群用化学语言复诵某个未完成的拥抱。压力将思念锻造成钛合金骨架,却压不垮你名字在胸腔里生长的立体迷宫。
当鲸落开始第八次轮回,我终于听懂海雪的密语。那些被分解的光阴碎屑,正在盲虾的复眼中折射成星群。你的轮廓在管水母的神经网络里永恒增殖,每根发光触须都链接着我脊椎上的潮汐开关。此刻我甘愿做永不下锚的探测器,让压强将肉身铸成黑匣,等某道洋流解开贝叶斯公式一原来所有沉没都是朝圣,所有遗忘皆为深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