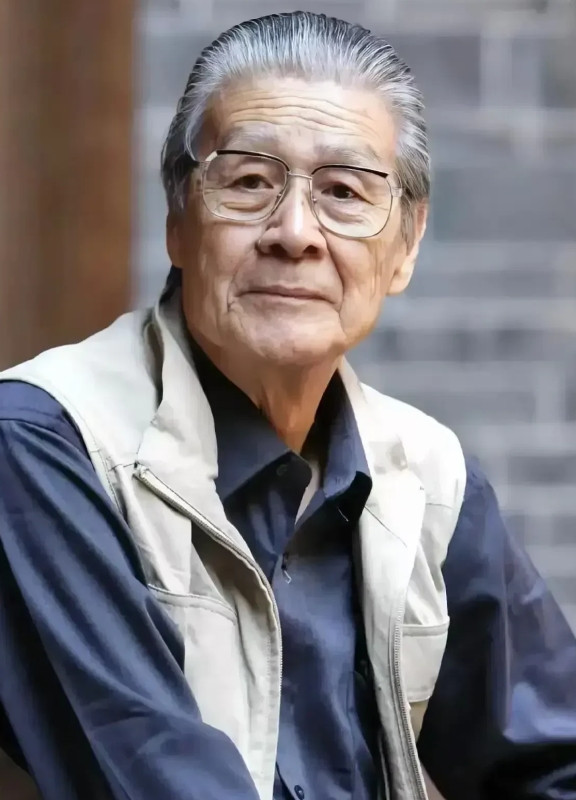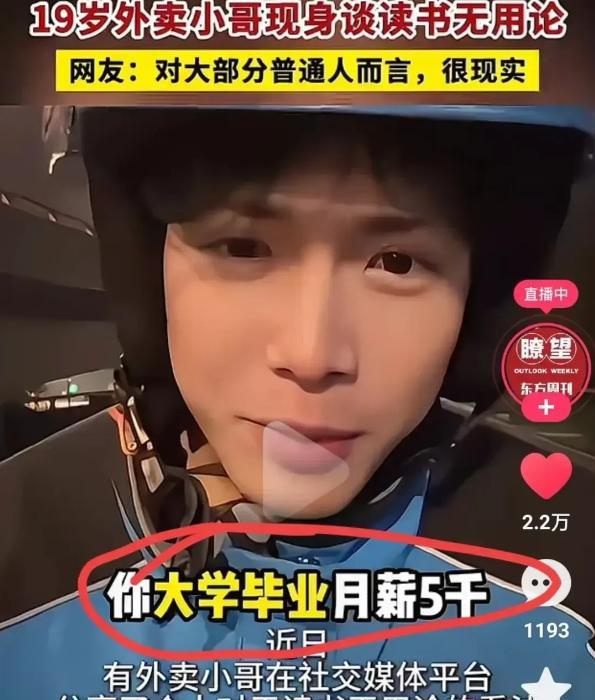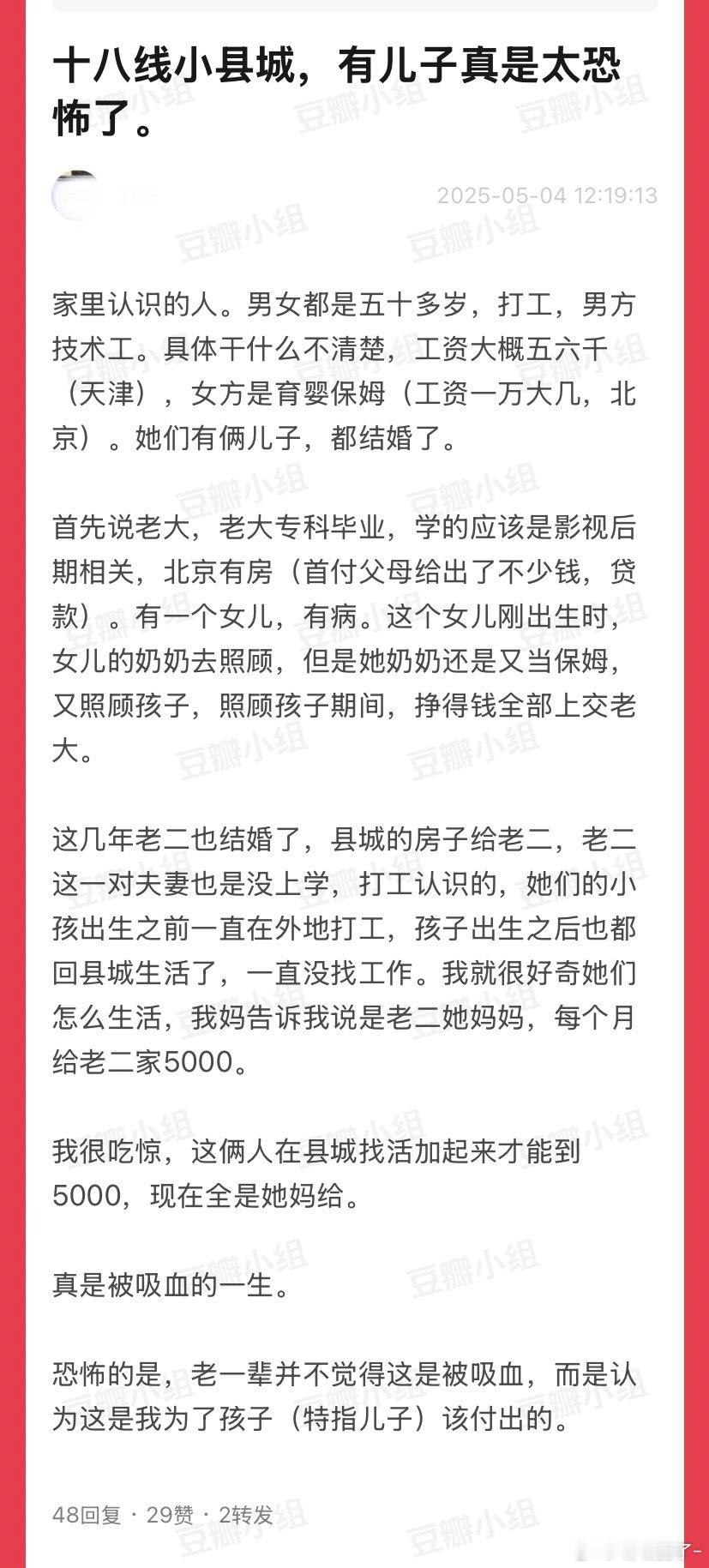1968年,严凤英趁着丈夫熟睡,来到床头柜前,将事先准备好的100片安眠药吞下,第二天一早,丈夫看到严凤英留下的遗书,马上叫了救护车,谁知等来的却是一群反动派,他们不顾劝阻,用斧头将尸体已经冰凉的严凤英开膛破肚,鲜血顿时喷涌而出。 1968年的一天,寒风像刀子一般在窗外呼啸,沉重压抑的空气充斥在每一个角落。 严凤英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手中握着一支笔,身旁摊开着一张洁白的信纸。 台灯发出昏黄的光,映在她略显苍白的面庞上,折射出一种近乎绝望的安宁。 她的笔划过纸面,一字一句写下诀别的言语。 字里行间,没有怨恨,只有不舍与无尽的疲惫。 “请原谅我的离去。我已经尽力了,但我实在再也承受不住了。请你,好好活着。” 这是她留给丈夫的最后一句话。 严凤英,这位曾经光耀舞台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如今不过是一位被时代所抛弃的“批斗对象”。 在那个风雨飘摇、是非颠倒的岁月里,曾经的荣誉、掌声、赞誉,如尘土般被人唾弃、践踏。 在那段时期里,艺人首当其冲,遭受了无穷尽的打击。 她曾凭一曲《天仙配》红遍大江南北,被誉为“黄梅戏皇后”。 但这份荣耀,在革命的铁锤下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毒草”,变成了群众批斗会上的罪证。 在一次次的审查与斗争中,她被迫低头、挨打、游街,曾经的剧团同仁,有的悄然划清界限,有的甚至落井下石。 她的丈夫是个导演,虽然竭力保护她,但在那个人人自危、祸从口出的年代,连最基本的温情也显得苍白无力。 他每天精神紧绷、如履薄冰,生怕一句话说错、一个眼神被误解,连累爱妻和自己。 可这一切,在严凤英看来,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她明白,他已经力不从心。 深夜时分,丈夫终于沉沉睡去,窗外风声低鸣,像是无声的哭泣。 严凤英站起身,走到床头柜前,那里放着她早已藏好的药瓶。 她没有犹豫,也没有颤抖,只是低头,仿佛饮下一杯苦酒般,一颗一颗将药片吞入。 过程异常安静,仿佛她的人生,也已在沉默中被定格。 清晨,丈夫醒来时,阳光从窗帘缝隙中透进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异样的静止感。 他下意识地转身,却看到妻子端坐在床边,头靠在墙上,脸色惨白,手中仍握着那封未折叠的遗书。 “凤英!”他惊恐地扑过去,触碰到的是一具已然冰凉的身体。 他疯了一样跑出门,呼救声划破清晨的宁静,让人将其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可来者,却不是医生,而是一群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 他们没有半点救援的意思,反而带着一种“执行任务”的冷酷。 有人翻看她的遗书,有人翻箱倒柜寻找“罪证”。 他们在屋中一阵大声吆喝,几人将尸体抬到屋外的院子里,一人抡起斧头,直直劈向严凤英的腹部。 “我们要看看这反革命藏了什么!”有人喊着。 鲜血在那一刻喷涌而出,染红了白雪覆盖的地面,她的肚腹被破开,内脏暴露在寒风中。 围观的邻居被这惨烈的一幕惊呆,几位老邻居悄然落泪,却不敢出声。 丈夫跪在血泊中,已然说不出话,他握着严凤英的手,泪如泉涌,却不知是为她悲,还是为自己、为这个疯狂的世界悲。 事后,这场“查证行动”不了了之,他们没在她体内找到所谓的“毒药”、“密信”或“间谍情报”。 只是简单地撂下一句:“她死得其所。”便扬长而去。 尸体被草草处理,没有告别,没有悼词。 唯一为她默哀的,只有那一院落雪未融的红地,仿佛她不屈的灵魂,在呼喊,在抗争。 多年后,风雨过去,人们终于开始为这段历史正名。 严凤英的艺术被重新肯定,她的形象出现在戏曲博物馆、电视纪录片中。 可她再也听不见舞台上的掌声,再也等不来一句“你是国家的骄傲”。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严凤英

![被坠落的直升机砸中的那个爸爸真是太不幸了,[哭哭]他的胳膊当场就掉落在了一旁,有](http://image.uczzd.cn/235122433091032495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