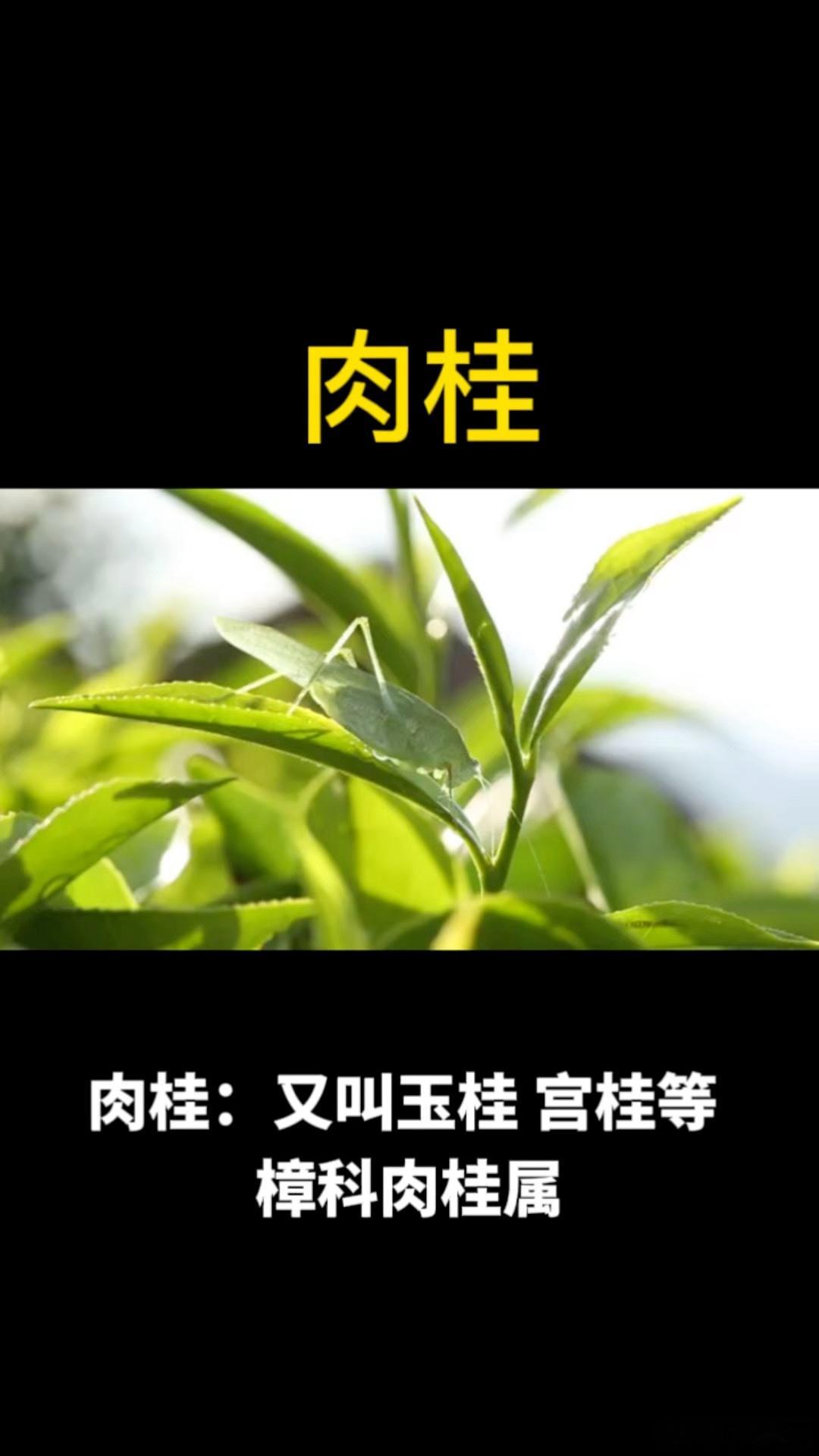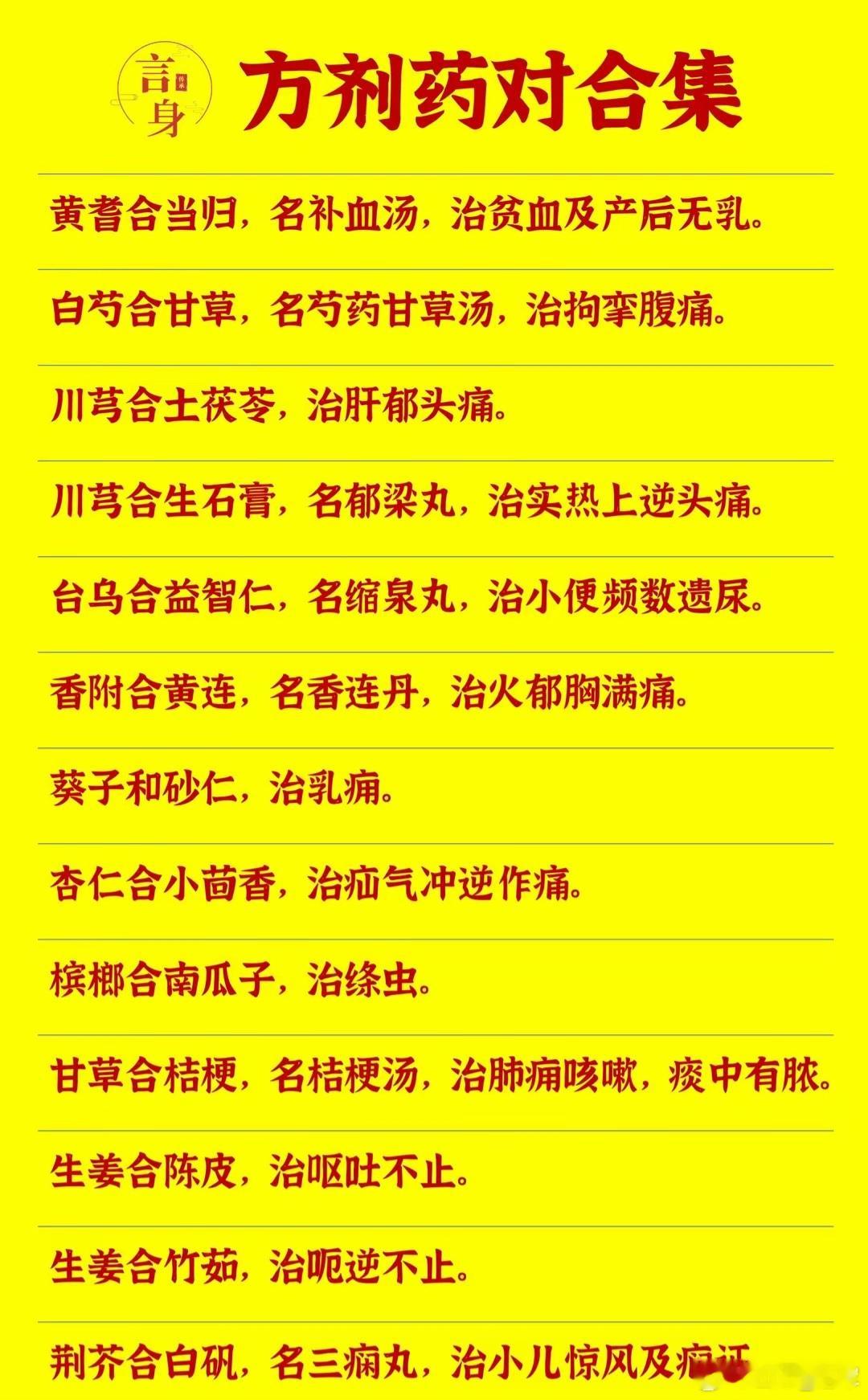为什么说“胃病先治肝”?从《医学正传》看气郁如何“拖垮”脾胃
《医学正传》关于胃脘痛有这样一段论述:“未有不由诸痰食积郁于中,七情九气触于内之所致焉,是以清阳不升,浊阴不降,而肝木之邪得以乘机侵侮而为病矣”。
可见,胃气之所以失于通降,是与肝气郁结、横逆犯胃息息相关的,同时与肺气的肃降亦有一定关系。说明气郁每能导致食积、痰浊、郁火和瘀血等病理变化。
一、核心病机:气郁为百病之始,肝胃不和为关键
1. 七情九气,肝失疏泄
忧思恼怒等情志刺激,首伤肝之疏泄功能。肝主气机调畅,肝气郁结则疏泄无权,势必横逆犯胃。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导致胃气壅滞,不通则痛。
临床特征:胃脘胀痛连及两胁,痛势走窜,与情绪波动密切相关,嗳气后稍舒,符合肝胃不和之候。
2. 胃气失降,清阳不升
胃以通降为顺,肝气犯胃则胃气壅滞,浊阴不降(食积、痰浊内停),清阳不升(脾胃运化无力),形成痞满疼痛、纳呆便溏的恶性循环。
此即《内经》浊气在上,则生䐜胀之理,与《医学正传》清阳不升,浊阴不降互为印证。
二、脏腑关联:肝肺同治,气机升降之枢纽
1. 肝木乘胃:气机横逆之根本
肝属木,胃属土,肝气郁结则木旺乘土,临床可见胃脘痛连胁肋、反酸口苦、脉弦等症。治当疏肝理气为主,如柴胡疏肝散(柴胡、香附、川芎)疏泄肝气,白芍、甘草柔肝缓急。
2. 肺胃相关:肃降失常加重胃逆
肺主肃降,与胃之气机通降相互为用。肺气失于肃降,则胃气上逆难平,可兼见咳嗽、痰多、脘痞等症。
治宜佐以轻宣肺气之品,如桔梗、杏仁,取提壶揭盖之意,此与叶天士治胃不忘宣肺之法相合。
三、病理演变:气郁致实,多邪交织
气郁作为始动因素,可衍生四大病理产物,形成虚实夹杂之候:
1. 气郁→食积
胃气壅滞,受纳腐熟失职,饮食停滞胃脘,化为食积。症见胃脘胀满、嗳腐吞酸,治当理气消食,如保和丸(神曲、山楂、莱菔子)消积导滞,兼以陈皮、木香行气化郁。
2. 气郁→痰浊
气郁日久,脾失健运,水湿内停,聚而成痰。痰浊阻滞中焦,则脘痞苔腻、恶心呕吐,治当理气化痰,如半夏厚朴汤(半夏、厚朴、茯苓)降逆化痰,紫苏叶疏理肝气。
3. 气郁→郁火
肝郁化火,灼伤胃阴,或胃腑气滞生热,形成肝胃郁热。症见胃脘灼痛、口干口苦、舌红苔黄,治当疏肝泄热,如化肝煎(青皮、陈皮、丹皮、栀子)清肝和胃,兼以石斛、麦冬顾护胃阴。
4. 气郁→瘀血
气滞日久,血流不畅,久病入络则成瘀血。症见胃脘刺痛、痛有定处、舌质紫暗,治当理气活血,如失笑散(蒲黄、五灵脂)合丹参饮(丹参、檀香),叶天士辛润通络法亦适用于此。
四、临床启示:治以调气为先,兼顾其他
1. 首重疏肝理气,调畅气机
无论兼夹食、痰、火、瘀,均需以理气为基础。代表方如越鞠丸(香附、川芎、苍术、神曲、栀子),一药解六郁,为气郁诸证之通治方。
理气当辨虚实:实证用柴胡、香附、青皮疏泄;虚证(如肝郁脾虚)用薄荷、陈皮轻疏,防耗气伤阴。
2. 随证治之,兼顾病理产物
食积重者,加鸡内金、炒麦芽;
痰浊重者,加茯苓、白芥子;
郁火重者,加黄芩、蒲公英;
血瘀重者,加桃仁、红花。
3. 调畅肺胃,升清降浊
肺气壅滞者,佐以桔梗、紫菀宣肺;
清阳不升者,少佐升麻、柴胡(如补中益气汤化裁),但需防升散太过耗伤阴液。
五、经典配伍解析:疏肝与和胃的协同
以常用方柴胡疏肝散为例:
柴胡、香附、川芎:疏肝解郁,理气活血,针对肝气郁结之本;
陈皮、枳壳:理气和胃,降逆止呕,解决胃气壅滞之标;
白芍、甘草:酸甘化阴,柔肝缓急,防理气药辛燥伤阴,体现“疏肝不忘和胃,理气需顾阴液”的配伍智慧。
六、结语
《医学正传》此论构建了“气郁→肝胃不和→多邪内生”的胃脘痛病机链条,强调治当以调畅气机为核心,兼顾肝肺同治、攻补兼施。
临证需详辨气郁之轻重、兼夹之邪实,灵活运用理气、消食、化痰、清热、活血等法,同时注重顾护胃气阴液,方得仲景随证治之之真谛。
此理论不仅适用于胃脘痛,亦为中医治疗气机失调相关疾病(如痞满、呕吐、胁痛)提供了整体思维范式。



![清阳升、浊阴降、脾胃和!一处方子带你轻松破解!升清降浊汤[加油]升清降浊汤它主要](http://image.uczzd.cn/4057705351361148767.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