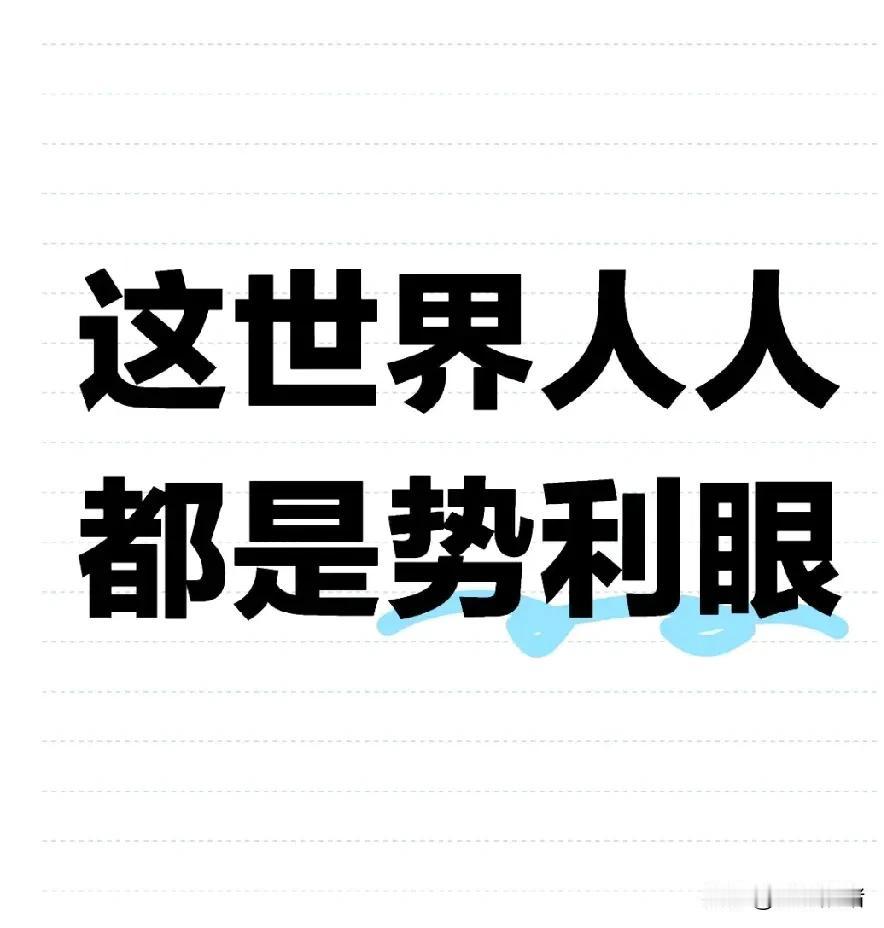1972年,钱三强走在街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突然拦住他。钱三强抬头一看,不禁惊呼:“老师,您怎么成了这样!”
1972年秋,北京街头。
钱三强穿一件洗得泛白的中山装,低头往单位方向走。布鞋踩在地上发出轻微的声响,他满脑子都是科研数据,没留意拐角处的动静。
突然,一个佝偻的身影晃到面前。
钱三强猛地抬头,见是个讨饭的老人:灰扑扑的衣裳补丁摞补丁,领口磨得发亮,袖口沾着饭渣;头发胡子结成绺,乱蓬蓬顶在头上;脸黑红粗糙,眼窝凹进去,眼珠发浑,却盯着他发直。
老人伸手拽住他的袖口。
钱三强碰到那双暴起青筋的手,虎口处有道陈年疤痕。四目相对时,他心里咯噔一下 —— 这双眼睛虽布满血丝,却藏着股熟悉的温和,让人想起清华园里总在实验室门口等学生的身影。
“老师?” 他喉咙发紧。
老人嘴唇哆嗦着,半天扯出个笑,嘴角往下耷拉,露出没了门牙的牙床:“三强啊,是你……” 嗓音沙哑,带着涩味。
钱三强鼻子一酸,反手握住那双手。
掌心的老茧磨得他生疼。当年在清华,这双手曾握着试管做实验,在黑板上写满公式,如今却粗糙不堪。他顾不上路人目光,拉着老人走到巷口石阶坐下:“您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老人叫叶企孙,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半数以上顶尖科学家,如钱三强、钱伟长、赵九章,甚至诺奖得主李政道、杨振宁,都曾是他的学生。 抗战前,他在清华园是儒雅的先生,总穿合身长衫,戴金丝眼镜,讲课时声音不高却句句清楚,外校学生常偷偷来蹭课。
学生病了,他送药;学生没钱吃饭,他塞饭票;学生论文遇到瓶颈,他在实验室陪到深夜。
可这一切,毁在学生熊大缜的事情上。
1937 年抗战爆发,熊大缜本要去德国留学。
叶企孙把他叫到办公室,窗台上的仙人掌正开着黄色的花。他摘下眼镜擦了又擦:“大缜,八路军缺武器,你学的炸药能派上用场。”
熊大缜没犹豫,转身去了冀中军区。叶企孙怕他人手不够,又动员一百多个学生,带着显微镜、烧杯等器材去了根据地。
熊大缜果真能干。
他带着工人用土办法造炸药,做出威力不逊色于进口货的烈性炸药。冀中军区炸药厂最多时有两千人,子弹、手榴弹、地雷成车往外运送。村口路边的地雷,炸得日军骑兵不敢轻易进村,老百姓说 “熊部长的雷比大炮还管用”。
灾祸从一场谈话开始。
1941年,国民党考察团来到冀中军区。专家方平跟熊大缜用英语聊技术,供给部政委王文波听不懂,看两人有说有笑,心中起了疑心:“都是中国人,为啥说洋话?莫不是通敌?” 这怀疑,成了大祸根。
国共关系恶化后,“锄奸” 运动兴起。
熊大缜被抓进土牢,罪名是 “国民党特务”。他喊哑了嗓子分辩,说自己造的炸药炸死多少鬼子,可没人听。1942 年的夜里,他被拉到河边枪毙,年仅 26 岁。
叶企孙得知消息,连夜冒雨赶到冀中。
他翻出熊大缜的炸药配方、实验记录、根据地嘉奖令,想替学生申冤。可那时,谁替 “特务” 说话 谁就被视为同党。1968年,他被关进牛棚,扫厕所、挨批斗,连一件像样的棉袄都没有。
冬天夜里,他蜷在水泥地上。
听着窗外北风呼啸,想起熊大缜临走前说 “老师等我胜利回来”,眼泪把草席洇湿了。
两年后他被释放,没了工作,没了户口。
他揣着破搪瓷缸上街要饭,夏天蹲在书店门口,冬天缩在胡同墙角。有人施舍块窝头,他就点点头,用漏风的牙慢慢啃 —— 谁能想到,这个浑身散发着酸腐味的老乞丐,曾是清华物理系主任,亲手培养出 79 位院士。
钱三强听完,拳头捏得咯咯响。
他想起在清华时,叶老师总把最新外文资料留给他,周末叫他去家里吃饭,师母会特意炖锅排骨。
现在看着老师衣不蔽体,他喉咙像塞了团棉花:“您等着,我找伟长、九章他们,一定把这事说清楚。”
接下来半年,钱三强跑遍北京各个部委。
他带着学生名单,挨个找当年的同事作证,连熊大缜当年的警卫员都找到了 —— 那汉子已是副师长,红着眼说:“熊部长死得冤啊,他的炸药救了多少战友!”
1975年,调查组进驻清华。
调查组成员看到叶企孙在牛棚里用烟盒纸记录的物理公式,以及他因被打断三根手指仍坚持书写的申诉材料,一时沉默了。
第二年,平反通知下达时,叶企孙正坐在钱三强家的藤椅上晒太阳,他摸着盖着红章的文件,缓缓说:“大缜可以安息了。”
1977年,叶企孙病逝。
追悼会上,钱三强颤抖着念悼词:“先生一生未娶,却把成千上万的学生培养成国家栋梁……” 说到 “成千上万” 时,他声音哽咽:“都是他的儿女。”
那些曾在硝烟里奔走的科学家,那些在牛棚里坚持计算的手,那些被岁月掩埋的冤案,终于在某个秋日,让世人看见 —— 师者风骨,如松如柏,纵经风雨,终见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