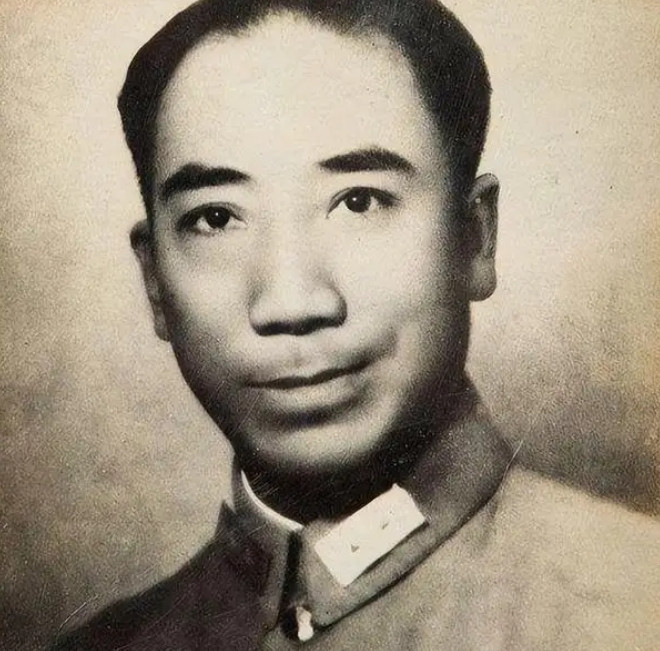1932年,陈玉仁突然叛变,向敌人供出了潜伏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感觉到不对,正准备转移,特务头子史济美突然破门而入!
王世英握着铜门环的手突然顿住,门缝里飘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焦油味,这是青帮暗号里"阎王要收人"的警告。他刚要转身,楼下传来门房老周变了调的吆喝:"史处长大驾光临!"
这个本该在南京坐镇中统上海站的史济美,此刻正斜倚在雕花铁门前,呢子大衣肩头落着层薄雪。
这位黄埔四期的同窗咧嘴一笑,露出镶金的犬齿:"听说王科长最近在倒腾古董字画?"他皮鞋尖踢了踢门廊立柱,"巧了,我表妹正缺幅吴昌硕的真迹。"
屋内正在烧文件的王世英手一抖,火盆里腾起的火星子差点燎着长衫下摆。三天前,印刷《红旗日报》的新生厂遭血洗,他亲眼看见总编陈玉仁被拖走时还在喊"我招供!他们都招供了!"。
"史处长说笑了,我不过是开个南货铺的。"王世英甩开长衫迎上去,袖口金表在吊灯下闪了闪。表盖内侧藏着微型胶卷,此刻正记录着史济美勾结日本商社倒卖军火的铁证。
特务头子突然劈手夺过紫砂壶,壶底"曼生十八式"的刻痕让他瞳孔骤缩。
1928年徐州剿匪时,正是这个纹样刻在顾顺章送他的勃朗宁手枪上。"王老板对茶道颇有研究啊。"史济美摩挲着壶身,"听说令正前些日子在霞飞路买了新宅?"
王世英后背瞬间绷直,妻子李果毅三天前刚搬进法租界新居,那里紧挨着法租界巡捕房档案室。他抓起茶壶猛灌一口,滚烫的茶水顺着喉咙滑进胃里:"托史处长的福,内人总算不用挤在亭子间抄经书了。"
话音未落,二楼突然传来瓷器碎裂声。史济美抬脚就要往楼上迈,千钧一发王世英抄起案头青瓷笔洗砸向电灯开关。
黑暗瞬间笼罩客厅,他趁机撞开暗门,顺着壁炉烟道滑向地下室,这是特科同志用三个月时间挖通的逃生密道。
"砰!"枪栓拉动的金属脆响在死寂中格外刺耳。
王世英贴着冰凉的砖墙屏住呼吸,听见史济美在客厅咆哮:"给我封了所有出口!那娘们肯定藏在隔壁百乐门!"
百米外的巷口黄包车夫老张猛蹬脚踏板,车帘后,李果毅攥着牛皮纸袋的手直冒冷汗,里面装着刚从巡捕房顺出来的二十七个共产党名单。
车轱辘碾过梧桐落叶时,她瞥见街角霓虹灯牌映出个熟悉身影——正是三天前刚被捕的陈玉仁,此刻正挂着"自首有功"的木牌游街示众。
这史济美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白手套",表面上是中央党部驻沪特派员,暗地里却是中统上海站站长马绍武。
1932年他刚接手上海滩,就给青帮大佬杜月笙递了帖子:"马某想讨教讨教码头生意经。"
没出三个月,法租界巡捕房档案室就多了本《中共地下党通讯录》,连闸北区委书记家的保姆生日都标注得明明白白。
最绝的是他搞的"细胞计划",专门培养中共叛徒当"活体探测器",当年顾顺章就是用这招把总书记向忠发送进了苏州监狱。
"王科长这铺子开得蹊跷啊。"史济美摸着博古架上的青铜器,"上个月查抄闸北印刷厂,搜出批印着《曾文正公全集》的传单。"
他突然抽出本账册,"巧了,贵铺子上月进货单上也有这本'古籍'。"
王世英心里咯噔一下,这本《曾文正公全集》的封皮里,藏着给中央特科的密电码。上个月交通员小王来取货时,分明看见史济美带着日本宪兵在仓库外转悠。
他捻着佛珠笑道:"史处长火眼金睛!要不我送您套线装版?"
说时迟那时快,楼下传来汽车急刹声!五辆黑色雪佛兰堵死了巷口,戴白手套的特务端着美式汤姆逊冲进弄堂。
史济美突然掏出手枪顶住王世英太阳穴:"王老板,令正现在应该正在霞飞路76号做客吧?"
千钧一发之际,厨房突然传来油锅爆响。王世英抄起烧火棍冲向后厨:"史处长稍等!刚炸的臭豆腐马上出锅!"浓烟中,他瞥见窗外飘过的蓝布衫——那是妻子约定的撤离信号。
"砰!"二楼传来玻璃碎裂声。
史济美踹开房门,只见雕花木窗大开,王世英的紫砂壶正骨碌碌滚下楼梯。特务头子冲到窗前,只见隔壁阳台上站着个穿长衫的胖子,正冲他晃了晃手中的怀表——表盖内侧"伍豪"二字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这是周总理亲自设计的接头暗号!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就用这招在南京城头换了三回密码本。
史济美眼睁睁看着目标消失在弄堂尽头,气得把勃朗宁摔在波斯地毯上:"给我全城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此时的王世英正缩在垃圾车底,腐臭的菜叶盖住他长衫下摆。车夫老张突然猛打方向盘,垃圾山轰然倾泻在巡捕房门口。趁着骚乱,他翻身跃上黄包车,朝着十六铺码头狂奔而去。
三个月后的南京雨花台,史济美盯着刑场上的绞架狞笑:"顾顺章这叛徒,连个像样的处决都安排不好。"话音未落,人群中突然闪过道黑影。
"砰!"邝惠安的柯尔特左轮喷出火舌,史济美捂着冒血的胸口栽下绞架。这个亲手策划了"东方旅馆爆炸案"的刽子手至死不明白:为何红队能精准掌握他的行程?
其实早在三年,1929年南京中央军校毕业典礼上,那个给他戴校徽的"教官",正是中央特科最早的情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