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刷到短剧《执笔》,好奇看了几集,然后就一晚上刷完了。平时不太看剧的我,终于明白磕CP为啥叫“磕”CP了!
这应该是个女频剧,大女主设定,女主不服被执笔的命运,一次次于水火中自救。剧情反转中,无可避免地出现误伤、利用、虐男主的情节。当然,无论怎么虐,男主对女主的爱都不会消失,甚至被女主推下悬崖,九死一生回来后还是要娶她。

这是什么,这就是比中彩票还难以遇见的无条件的爱,它的光辉可以亮瞎所有人的,爱的圣杯。
在这基本的心理需求上,爽剧让人更爽的地方在于,男女主都是高颜值(有些还是高出身),心里爽,眼里爽,那就是倍儿爽。
我发现自己看剧,尤其在看男女主的互动情节时,会控制不住地嘴角上扬,某种暖洋洋的气泡在心窝泛滥,或如某条弹幕姊妹所说“剧情很紧张,但我忍不住的姨母笑是怎么回事”。
刷完剧后,一想到剧里的画面,那暖洋洋的气泡便洋溢全身,仿佛自己也是被爱着的,心情暖暖的,连世界都变得更美好了。
刚好最近在看《梦瘾》,一部讲述美国阿片类药物、海洛因上瘾的非虚构纪实作品。有一种阿片类药物叫奥斯康定,它有一层包衣,可以在人体内缓时释放。
这短剧的CP情结,就像被吸收到体内的药丸,它一阵一阵缓时释放着“吗啡分子”,让人沉浸在温暖气泡的愉悦感中,体验着漂浮于现实之上的幸福。
啊,终于明白CP为什么是用来“磕”的了!
话说回来,这部短剧体验我很喜欢,同时它也成为我近期思考的其中一块拼图,也就是关于此篇文章的正题——即真实自我。
什么是真实自我?
和以前不一样,我发现这次短剧带来的爽感它有着清晰边界。
如果说短剧世界是一层楼,现实世界在它楼下的话,这次我的感受是,楼上的我可以尽情沉浸在CP爱的泡泡浴里,泛滥的洋洋暖意并不会影响到楼下我的日常作息、行动思考。
换做以前,这种暖意大概率会蔓延到楼下,成为某种期待,比如影响少女时期的恋爱观。现实里,期待有可能会演变成落差,最后就是幻灭的泡泡。
这种落差感可能来自于对外界的认识,“又有颜值又有身世又不介意被虐的对象,我找你找得好苦啊…”,也有可能来自于对自己的认识,“凭什么这么虐我还要我无条件去接纳你,我最爱的是我自己啊…”
一边渴望无条件的爱,一边又给不了无条件的爱,下一步走向便可能是内耗了。
如果用一个画面形容内耗,我觉得那便是失去楼层架构的大楼,不同楼层的“我”们开始上下串楼,飞来撞去。虽然表面看这幢楼还在,但楼里的东西已被撞得七零八落。这楼里的状况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虽然内耗耗能,但它确实也是我们认识自己是谁的良好契机,或者说,是认识我们身体里不同的自己们的良好契机。可谓,不撞不相识。
什么是真实自我呢?我的理解就是那住着不同自己的N层高楼。
有一层的我乐观,有一层的我悲观;
有一层的我想要运动,有一层的我想要躺平;
有一层的我觉得孩子可爱,有一层的我觉得孩子可恶;
有一层的我有着人类本能里的对无条件爱的渴求,有一个层的我感受到的是日常和人相处里的需求…
真实的我,它从来不是一个人。俗语说一粒沙中见世界,以此类推,一个人里可见宇宙。
这宇宙里,有恶有善,有动有静,有横轴上从古至今的人类潜意识、欲念、本能,也有竖轴上现世的三观、理想和抱负。
真实的我,不是某个人设,也不是某种特质,它是所有时空面向的集合体。
和人聊天,有时会听到别人说“哎,我这人就是这么矛盾”,活动里感受别人的故事时,矛盾二字也会频繁出现。以前提到这个矛盾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往往是在指出某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所带来的“拧巴”“纠结”。
现在想想,其实“拧巴”“纠结”的时候,反而是离真实自我更近一步的时候,因为我们又看到了自己的另一个面向。
人生阅历,便是我们不断捡拾起不同自己的过程,一个一个地拼凑起来,构筑和还原出完整的真实。我们捡拾起的,可能小如刹那的心念、思绪,也可能大至整块的情感和人格。
真实自我,它原本便是完整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宇宙,它不是小宇宙哦,而是真正的宇宙。

什么是看见自我?
上上周去看了电影《功夫熊猫》,阿宝在树下打坐的时候,他告诉自己要“心如止水”,结果一口气还没呼完,脑袋里就马上窜出了各种念头,好几个会说话的熊猫头环绕着阿宝,一个声音变俩,俩变四,四变N,最后一片嘈杂。这种时候,只能崩溃到要大叫一声。

另一个场景是和朋友聊天,TA说这几年慢慢看到了自己的真实,这个过程相当痛苦。你会看到自己的嫉妒,那些丑陋的部分。我听到TA用“不好”“丑陋”来形容自己看到的,我问TA,那你看到这些后是什么感受,TA的回答出乎意料,TA说“我自由了”。
都是听见自己的声音,一种是崩溃,一种是自由,为什么呢?
我目前的理解是,阿宝听见了声音,但他是被动地去听见,他是听到杂念而不是看到自己,甚而有种想要压制声音的姿态。而后者的朋友,TA不是压制,TA是允许,允许“丑陋”的、“美好”的自己都能发声,谁都别憋着,人人机会均等。
以往,那些“丑陋”声音被道德、对错、对自我的完美形象压制着,它们和美好面一样都是客观存在,却很少有过平等的发声机会。长久处于憋屈状态,不得不说,这些“丑陋”自我也会产生怨念,没法发声的它们便有可能通过无形的怨念来影响甚至控制其他自我的状态。
就像有心事的我们在和别人倾诉过后,内心会畅快很多一样,“丑陋”自我在得到倾诉空间后,它的憋劲和怨念也会得到释放。释放了自己,也释放了对其他自我的负面影响。每一个自我都可以纯粹成为它自己。
盲猜,这大概是朋友所体会到的自由。听见“丑陋”的声音,但不是被它吵到,也不是被它控制,而是承认并尊重它的存在后,每一个自我都获得了被看见后的满足感。自我之间的负面羁绊减少,没有谁要去消灭谁,也没有谁要去评判谁。
插开一句,话说一些人谈到真实自我的时候,可能更多是一种相对概念,相对于那个被规训于社会时钟、遵循着社会角色脚本的自己。和这个“规训我”相对的,是不受约束去做自己想做事情的那个“心意我”,很多人会觉得后者才是真实自我。
有所区别的是,这篇文章所论及的真实自我,会认为以上情境下的“规训我”和“心意我”,它们其实都是真实自我的部分。
一个人有想从众、获得社会认可的需求,也会有想自在地去做选择的渴望,这两者都是客观存在的。“规训我”没必要羡慕“心意我”,“心意我”也没必要鄙视“规训我”,因为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真实。没有必要谁要去消灭谁,也没有必要谁要去评判谁。
话说回来,当负面羁绊减少,各自得到满足的自我们便不再闹腾,如银河系的天体,它们在各自楼层轨道里井然运行着。这静下来的空间,便是朋友TA的自由之地了。
《写出我心》一书里,作者娜塔莉描述道:
“如果你内心的多个角色想打架的话,就让他们打吧。在此同时,你内在神志清楚的那一部分应该悄悄地挺身而出,拿出笔记本,从比较深沉、比较宁静的地方写起。
可惜的是,那两个打架的人常常跟着你来到笔记本旁边,他们毕竟活在你的脑袋里,我们可没办法把他们留在后院、地下室或托儿所。
因此,你可能需要给他们五或十分钟在你的笔记本上发言。就让他们写吧。妙的是,当你给这些声音写作的空间时,他们的怨言很快就变得枯燥乏味让人烦腻。”
于是闹腾又回归到了宁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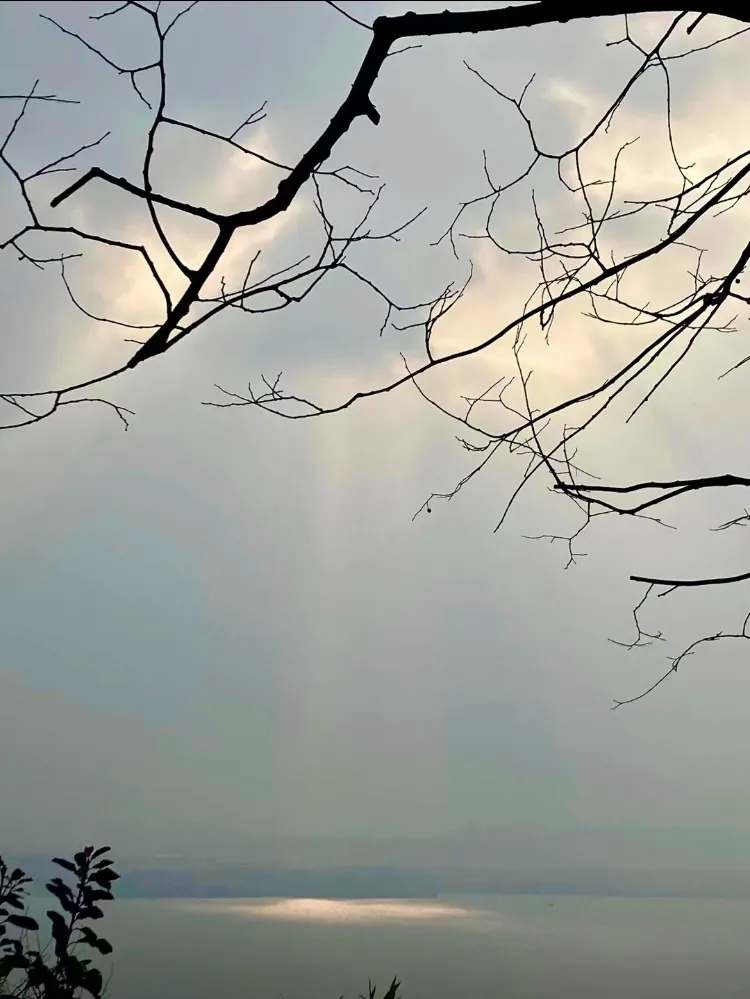
自由,并不一定都得向外去寻找,这里有一份自由,是我们可以给予我们自己的——那就是恢复每一个自我的发言权,给予它们相等的尊重,在自我的国度里实现对自由的解放。
如何看见自我?
恢复每个自我的发言权后,我们可以听见很多声音,那如何从听见走向看见,并不止于看见呢?
类似《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一书里所提到的“三步走”:“第一阶段是设别神经质倾向,第二阶段是'发现其原因、表征以及后果',第三阶段是'发现它与人格的其他部分、尤其是与其他神经质倾向之间的相互关系'”。
上述段落的语境是关于精神分析的,但我觉得它也可以脱离这专业语境,用于日常的自我认知。
第一步,听见并识别出自己的声音。
第二步,让这个自我发声,倾听它,理解它,试着进一步纵向深挖这个自我背后是否有其他动机或考虑。
第三步,横向感受它和其他自我的关系是怎样的,是良性互动还是负面影响,还是平衡牵制呢。
我自己在阅读《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时,有过一次这样的发现。
在和人相处里,我感觉到自己有善意一面,不想有冲突,某些事情上有较大宽容度,一般正常人不会无缘无故说想做个坏人去伤害别人之类的,我听见内心说要善良、要懂事的声音。
后来,我发现这份善良背后,除了善意的姿态,在某些情境里其实还有另一种姿态,那就是软弱。
这时候的让渡或宽容,其实不是为了别人着想了,而是力量差距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这是更深一层的看见。当我看见那个软弱的我躲在善意背后发抖的时候,我明白了原本的善意为何会带来委屈。
当“软弱我”的这份委屈,被“善意我”这层表面动机遮盖起来的时候,委屈的底色好似化成了阴郁雾气,在自我的大楼里蔓延。
你会发现其他自我好像也没那么纯粹了,身心渐渐被蒙起一层灰样。你能看见绿色的春天,但无法直接感受那一直就蛰伏在身体里的喜悦本质。
当“软弱我”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拥抱和安抚后,尽管它无法一下子恢复到它的自由状态,它也在一天天恢复起自己的力量了。大楼里的阴郁底色渐渐褪去,我能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更多面向,也得以重新看见那颗恒常里的喜悦之心。
整个人的力量感不是由某个“强大我”或“正能量我”单独给到的,它的根基来自于全体自我的相互看见,和牵起手围起来的平衡。
我很喜欢《图解瑜伽经》里提到的一个比喻:
“心念不是自明的,它不像太阳那样是光明的给予者,而是像月亮一样是光的反射者。这个光的来源即是灵魂,心念只能借着灵魂反射的光才能发光和感知。”

(心念之光,如月 / 来自网络)
如果自我发出的心念,是来自灵魂的折射,那它们不仅是认识真实自我的指引者,还是导向我们灵魂之路的北极星。这就是,不止于看见。
那看见之后呢?
在我有限的冥想练习经验里,我的脑海如阿宝一样,总会浮现出各种声音。我听到要旁观心念的教导,于是不管不顾,就这么看着,到后面也不知道是在看着,还是也有在悄悄参与生产了…这个过程并没有留下多少安定感。
读到《图解瑜伽经》时,里面提到:“瑜伽不止是阻止或减少万千思绪。事实上还需要正确地引导和运用心念。”
引导和运用,这俩词我很喜欢。
《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里说:“我们首要的道德义务不是压制某种天生的恶或原始本质,也不是驱使我们自己去企及不现实的理想或戒律,而是为了'在自己身上下功夫',为的是在成长过程中摆脱种种破坏性倾向。这些倾向是反应性的,而非先天的,从而实现我们的潜在能力。”
这段话像是对“引导”和“运用”的后续解释。不是压制、控制、规制,而是引导那些我们后天形成的破坏性倾向,让它们不至于真的产生破坏性影响。这里,我个人觉得破坏性倾向除了后天形成的,先天本能或欲念里也会存在。比如之前朋友提到的嫉妒心。
对以上两段话的消化吸收后,用我自己的体验来理解,那就是看见自我之后,要做的便是对自我们的整理和收纳。也就是把之前打乱的楼层、四处乱飞的“自我”们重新一层层地归置好,让每一个都去到它各自应有的空间里去。
这次短剧《执笔》的观影后遗症没有渗透到现实,带来所谓的“落差感”,便是因为我把洋溢的泡泡都归纳在了本能需求层,它的可能性和我的现实生活有着清晰边界。
在引导了它的破坏性倾向后,另一方面,这份爽感带来的爱的暖意却也是实在洋溢到了我的身心。那两天出门,我感受到自己是真开心,虽是雨天,但世界也是美美哒。这里要感谢下《执笔》带来的好心情~
那么,如果要整理和收纳那么多的心念、自我,这工作是由谁来做的呢?
这里要提及一篇文章,个人感觉文章作者的论述甚是精彩。这篇文章题目是《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一座浩瀚的迷宫》,作者说:
“那么这场议和会议的主持人(大安注:也即我所说的自我整理和收纳)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心神'。
心神其实是一股合力,是身体里诸多子人格共同形成的一种类似于集体意识的东西,就好像每个人的身体里都住着一个男团或者女团,心神就是这个'团魂'。心神不参与权力游戏,可以保持立场,大家都服它主持公道。
当一个人心神涣散,我们形容为'魂不守舍',其实身体里的各种子人格就进入群龙无首的争夺主权抢麦模式了。ego角力,邪念占据心神,就有可能变成了'心魔',一路用执念带着画风越跑越偏。
人格整合的学习,其实就是内在精神向心力的凝聚,通过内部的自我沟通与和解,去唤醒'心神'这个合力。”
这个主持人,不是所谓的“超我”,也不是“理性我”“智性我”或“灵性我”,个人觉得这种种“我”尽管存在层级、性质的区别,但它们也只是真实自我的其中一部分。如作者深蓝所说,这个自我们的收纳者不是任何一个“我”,而是“我”们所形成的合力。
这种合力所带来的结果可能如《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里所说的:“他知道自己真正想些什么、感觉到什么、相信什么;他能够对自己负责,决定自己的价值和生活目的”“我们也就能够使自己自由地去爱、去关心他人,我们自发的行为方式亦将促进他人的成长”。用另一句话来概括,即是对真实自我的实现。
抛开书本描述,于我个人而言,这种合力让我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体验意识,那就是——去体验作为一个人的体验!
体验作为人的每份情绪、每个念头,体验心血来潮,体验懒散躺平,体验杂念,也体验放空。既然有缘来到人世,这不应是我为人一趟的最主要目的么。至于是否能助及他人、做出社会价值,这些都是这份做人体验中所带来的衍生品了。
前几天和朋友聚会,我说到自己的这份体验感悟,TA说是不是类似于之前提到过的“和焦虑共处”。我想了想,发现姿态类同,但细节有了些许变化。
共处,是我可以看见某个自我,但同时也和它划清界限,不想让它来影响到我的生活;
体验,依然是有界限的,依然可以看见某个自我,但这个时候,我已不介意跳入这个自我的世界去沉浸一番,因为我获得了更多可以自由出入不同圈层的力量了。
我把它当成自我合力成长过程中的礼物。
当我们每天像整理书桌或卧室一样,小小打理、收纳下我们的自我空间,也许年底也不需要太费劲地大扫除,也就是去走入更大规模的疗愈。
古希腊有则神话,代达罗斯这位雅典发明家曾在克里特岛为国王米诺斯建造了一座迷宫。迷宫里面有凶猛的半牛半人怪。代达罗斯和儿子伊卡洛斯失宠后,被关进了迷楼,唯一的办法就是做对翅膀,飞出去。
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里说,那怪物象征欲望,迷楼象征社会。我突然觉得,如果放在自我语境下,那怪物似乎就是我们内心的破坏性倾向,而迷楼则是一层层的无数个不同面向的自我们。
重要的是,这座迷楼是我们自己建的,而它囚住了我们自己。

年轻的伊卡洛斯飞出来了,但他忘记了父亲的告诫,他飞得太狂太高,蜡制的翅膀被太阳融化,他坠海而亡。
飞得过高,翅膀会被高温融化,飞得过低,则会被海水濡湿,木心先生说,年轻的伊卡洛斯不懂,他父亲是老艺术家,懂。
言外之意,我感受到的,是年龄和阅历带来的人生内核,即稳定的自我合力,那可以自如于烈日和冷海之间的平衡之美。
*有感而发的相关资料们:
《梦瘾》, 山姆•昆诺斯著, 2021年
《写出我心》, 娜塔莉•戈德堡著, 2016年
《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 伯纳德•派里斯,著, 1997年
《图解瑜伽经》, 帕谭佳里著, 霍华德译, 2007年
《文学回忆录》, 木心口述, 陈丹青笔录, 2013年
《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是一座浩瀚的迷宫》, 公号文章深蓝撰文
王大安
场域活动孵化人 / 非虚构写字者
记录探索真实的自我和世界
凡真实的,必会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