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li { white-space: pre-wrap; }
大楚蛮夷:4、周公的东征
鬻熊死后,楚人首领之位依次传至其子熊丽、其孙熊狂、其曾孙熊绎。
同鬻熊一样,历任楚酋都效忠周国,带领族人们参加过孟津会盟、牧野之战,为剪商大业立下一些功劳,但在论功行赏、分封建国的时候,周武王却唯独将楚人排斥在外。
熊绎也不计较,他明白自己只是一个小酋长,大家眼中的南蛮,同那些立下赫赫战功的、与周王有血缘关系的功臣有云泥之别,周室能把你当自己人看待就是天大的面子,再提要求就是得寸进尺,不讲政治。
人在屋檐下,处处得低头。熊绎寻思留下来也没多大进步空间,干脆哪来的打哪回去,跟周武王辞行后回到老家务农。
原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平静的生活再不起波澜,但命运的转折不约而至,谁也无法预料。
几年后的一天,在家赋闲的熊绎做梦也想不到,有个功盖天下、权倾朝野的人会翻山越岭的来拜访他。
他就是周武王四弟,周公旦。
历史上有很多功德名望至高至上的贤臣,比如伊尹、管仲、百里奚、孙叔敖等,他们就像天空的北极星一样,显耀一时,但无论怎么耀眼,他们也只是一颗星,夜空最强的光芒,还是月亮。
皓月当空,月明星稀。
周公旦就是照耀古今的长空皓月。
贾谊:“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先秦时期的人崇拜鬼神,灭国之战也多是采用“灭国不灭祭”的做法,如果将一个宗庙的人全部咔嚓,断了香火,就没有人去祭祀他们的先祖,先祖的灵魂只能流浪于天际之中,化为孤魂野鬼,降灾于肇事者,这是十分恐怖的事情。
纣王之子武庚便是“灭国不灭祭”而存活下来的商室遗孤,周武王将其分封在商旧都朝歌,主要的任务便是祭祀殷商先人,管理殷商遗民。
为了防止武庚等殷商遗民叛乱,周武王又在朝歌周边设立了卫、鄘、邶等三国,分封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等三人共同监视武庚,史称“三监”。
不久,周武王还没来得及立遗嘱便暴毙,王位空缺,按照夏制的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世袭制,周武王的儿子姬诵和他的三弟——三监之一的管叔都有可能坐上天子宝座。
姬诵年幼,不足以执政。盛年的管叔神采奕奕,被很多的人看好。包括管叔自己也很看好,早早收拾行囊,只等任职文件下来便返朝履职登基。
等待的过程是幸福的,也是无比煎熬的,唾手可得的权力让人又爱又恨魂牵梦绕。
但命运的垂青始终和管叔擦肩而过——周王室最终决定年幼的姬诵继天子位,是为周成王。年纪小不打紧,找个权臣来摄政,待天子长大后再将权力还给他不就行了。
摄政之人,就是周公旦。
《礼记》:成王幼,不能莅阼,周公相,践阼而治。
周公摄政,天下大乱。
内外都有。
大乱之一,来自被命运遗弃的管叔。
眼看将要黄袍加身,风光无限,却最终失之交臂,如堕深渊。
希望和绝望的落差足以让人铤而走险,对权力的仰望更容易让人迷失心智。
管叔一脚已深陷欲望的泥潭,正确的做法是及时抽脚上岸,甩干淤泥,正视自己,但追权逐利乃人之本性,他的最终选择是将另一只脚义无反顾的踏进泥潭。
等待他的,只能是垂死挣扎。
管叔联合其他二监,又发动一帮兄弟,刻意抹黑周公旦,在舆论上对周公旦施压,甚至做好了清君侧的准备。
《尚书·周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
大乱之二,来自亡国的武庚。
对所有的商人来说,商朝的灭亡只是一个意外,如果不是奴隶临阵倒戈,如果不是内奸微子启通风报信,如果不是大军远征东夷,朝歌绝对能撑到大将飞廉的救驾。
满手好牌因为一子错张而满盘皆输,复盘再来是所有商人的迫切心愿。
武庚趁机迎合管叔等人,召集旧部,准备复辟。
两千多年来,亡国又复国的国家万里挑一,从时间上说离商末最近的只有越国成功复盘,但那也是因为有楚国的扶持,这充分说明一点:
历史不是回合制,更没有复盘一说。
管叔和武庚,为了不同的目的狼狈为奸,蠢蠢欲动,意图推翻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周王室。
大乱之三,来自王室内部。
王室贵族也开始对周公旦摄政持怀疑态度:周朝初立,政权未稳,一旦周公旦羽翼丰满,撕下摄政这块遮羞布,演化为篡位也不无可能。
并且权力这个东西一旦附体,就像脆弱的寄居蟹找到了坚硬的壳子,横行霸道,一旦钻出壳子就暴露了柔软的腹部,任人宰割。
丧权失利基本和身首异处划等号。
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也使周公旦处境举步维艰:管叔执政,势必会引起姬姓诸侯与异性诸侯的对立,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周成王就不同了,他的外公是姜太公,由他执政将会巩固姬姓的统治稳定。
是效法古制还是稳定压倒一切?
是着眼当下还是展望未来?
真让人头疼的单选题。
但,留给周公旦的时间不多了。
公元前1042年秋,武庚串通管、蔡、霍三人,联合东方旧属奄国(今山东曲阜旧城东)、蒲姑(今山东博兴东南)及徐夷、淮夷起兵反周。叛乱势力遍及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
“风雨所飘摇,予唯音噍噍”,周国正准备接受建国以来最严酷的考验。
严峻之下,周公旦不但不回避质疑,反而还向姜太公和召公阐明了自己观点,坚持认为扶立周成王代行天子职权是为了巩固三王基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为了江山社稷。
效法古制不一定稳定,稳定不是从一不变,是需要动荡中求发展,发展中求突破——不破不立、破中求立。
在姜太公和召公半信半疑之际,周公旦表态:待周成王冠礼之前,一定会交出所有权力。
统一了内部意见之后,周公旦积极采取措施,率卫队西六师兴师平叛。
论治国水平,周公旦当之无愧第一;论军事能力,不输姜子牙。仅一年时间,周公旦就平定了三监之乱:殷商余孽武庚被咔嚓,造反头子管叔被咔嚓,蔡叔被流放,霍叔被贬为庶民。
在规定时间内,周公旦交出了满分答卷。但他没有自满,他想冲刺附加题。附加题一旦出错,满分答卷作废,因为附加题主要内容是——赌国运。
当初武王剪商之后,为笼络人心,对宗室和功臣大肆分封,但问题的关键也出在这:周国也就是灭掉了商都而已,商在东土尚有大量的亲商和同盟势力。
所谓的分封,只是把纸面上的地盘分给诸侯——指着地图一顿猛操作,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地盘,先把蓝图规划好再说。
换句话说,就是打白条。
没办法,实力不够,画饼来凑。
白条总有挤兑的一天,杠杆加的再欢,逾期就算赔光裤衩也还不清债,每当武王想到这些旧账都心烦意乱,夜不能寐,担心过度,不久撒手人寰。
《史记·周本纪》: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武王病。
平定了三监之乱之后,周公旦认为时机成熟,是时候兑现白条了,于是组建了殷八师,兴师东征,兵锋直指东夷诸国。
三年时间,周公旦率领殷八师一路所向披靡,商将飞廉伏诛,“天下大悦”。又灭奄、丰、蒲等大、小方国五十余,徐、淮等东夷势力望风而逃。
东征的战斗是残酷而激烈的,《诗经·豳风·东山》就是以周公东征为历史背景,以一位普通战士归家前复杂的内心感受,来抒发对战争的思考和对人民的同情。
不放译文了,体会下这篇真致细腻的作品。
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仓庚于飞,熠燿其羽。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
为了彻底消除商朝残余势力对周朝的隐患,周公旦又在洛水北岸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周的东都,以便于加强对东方的统治。
如果说之前武王克殷靠的是出其不备,打击了商王室的核心部分,那么这次周公旦东征,完全是面对面的与殷商及东夷的主力硬杠,用实力兑现了白条,立下不朽功劳。
周公东征也是周朝的立国之战。
此后,各路诸侯按照事先的分封在中原大地殖民掠地,开创大周王朝,成为东至东海,南至淮河流域,北至辽东的泱泱大国。
天下归心。
三监之乱这件事深深的刺痛了周公旦,他认为乱的原因是夏商的政治制度出现了漏洞,这些漏洞又成为野心家获取权力的掌中尤物,乐此不疲。
深思熟虑之后,周公旦决定修改延续自夏以来的政治制度,否则周朝就会卷入无休止的内耗,还没等外敌动手,自己就两腿一蹬,完犊子了。。
漏洞必须补上!
一个全新的制度改革在他脑海中形成。当孔子无比向往地说出那句“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时候,他指的也是这件事。
一个国家不可能久盛不衰,消亡是其历史规律,但伴随一个国家产生的文明,却能如银河一般承载万亿星芒,成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和凝聚力。
它,就是影响和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制度——礼仪制度。
未完侍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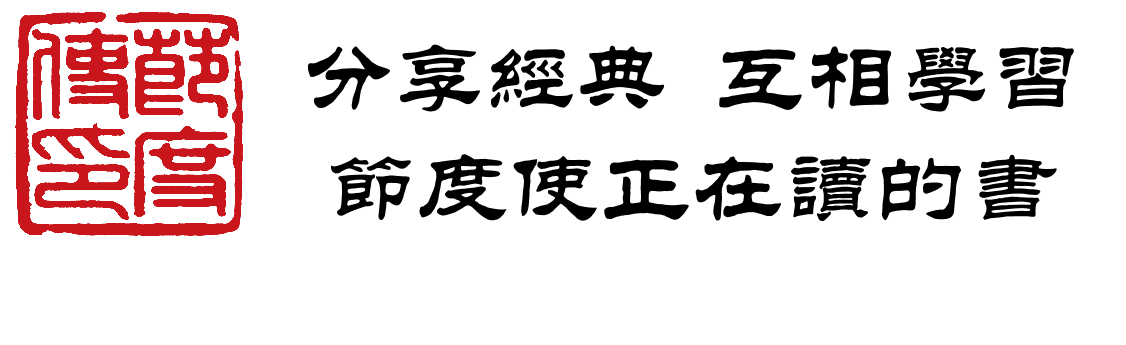
本文选自文章《 大楚蛮夷》,已获授权转载
作者:躺在屋顶数星星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